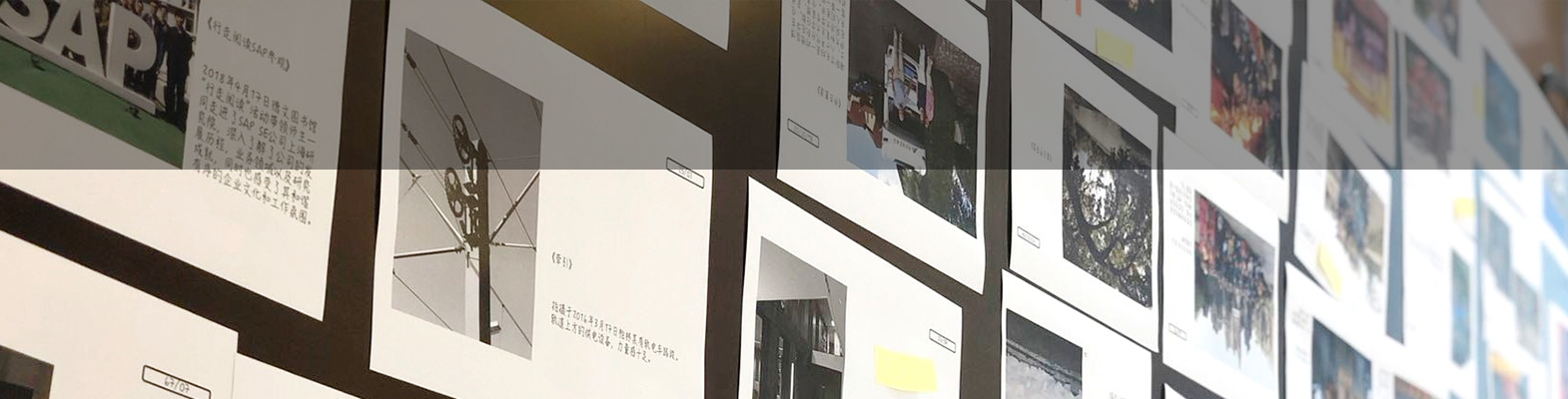本文原刊《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1. 鲁迅德文藏书中所藏谢来耳的《世界文学图史》1900
内容提要 在鲁迅的德文藏书中,《文学通史》和“瑞克阑姆小文库”占据重要的位置,给予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以丰富的文学滋养。基于德国民族主义和建立联邦德国的政治理想,文学史家谢来耳在其影响深远的《文学通史》中提出“日耳曼地区文学”的概念,提倡在德国领导下、由日耳曼地区各民族文学组成的“世界文学”。瑞克阑姆出版社的出版资本又进一步使德国的“世界文学”得以在全球消费和流通,远播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资本、理论和政治力量三者齐头并进,共同构筑19世纪德国的“世界文学”空间。这一“世界文学”空间进入留日期间鲁迅的视野并形成日后的“弱小民族的文学”。

2. 1899年8月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的德文杂志《文学的反响》,鲁迅在上面读到了对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的介绍。
鲁迅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翻译家。据不完全统计,他曾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将近一百多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总字数达到两百五十多万字,数量与他自己的全部著作大致相等①。其所翻译的作品主要来自俄苏、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弱小民族”。鲁迅这部分翻译几乎都是据德语译本进行的重译。因此很自然,至今尚可见的鲁迅西文藏书以德语为主②。据周作人介绍,那些作品大都来自被帝国主义大国兼并的弱小民族,他们的著作很少被翻译为英文,只有德文译本还可见到一些③。同时,周作人还提到两部德文的《文学通史》曾给予留日期间的周氏兄弟很大帮助。留日时期的鲁迅很可能一边阅读当时能找到的德文版的“世界文学史”,一边据此进一步搜求德国各个出版社的文库和作品集。
过去的不少研究已经注意到德文图书对鲁迅翻译的重要性④。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何这些“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德文中较多见,这些“弱小民族”在德语世界文学史中的原始面貌又如何?目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较少,使我们对“弱小民族的文学”是如何从德文世界流转到日本以及鲁迅是如何通过德语译本接受“世界文学”的历史语境知之甚少,也使得我们目前对鲁迅视野中的“弱小民族的文学”的理解较为抽象,对其诞生的历史脉络关注较少。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考察当时的“世界文学”在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建构和流转情况,将“世界文学”看作是时间和空间流变的产物。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通过对欧洲现代文学(主要是法语文学)的研究,提出了“文学空间”(literary space)的概念,认为文学有领土和疆界,决定一种文学为何在此而非在彼、以何种面貌出现,除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外,还受到翻译、文学语言、评论、出版商、美学特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互相关联的文学文本会形成一个内部充满争夺和竞争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有时这些影响还是交叉和多层次的。例如,西班牙作家贝奈特是通过法语阅读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作品的,这并非由于其对法国或法语的迷恋,而是因为讲法语和阅读法文是西班牙作家能够进入文学市场的保证。而其阅读美国作家的作品也并非出自对美国现代主义的兴趣,而是由于福克纳在巴黎的突出地位。而贝奈特此后努力在其自身的西班牙历史中找到和福克纳笔下的美国的相似性,实现文学问题和主题上的复制。通过法语和法国文学的中介,贝奈特和福克纳这两个表面完全隔绝的世界出现了惊人的吻合⑤。诸如此类的“福克纳在拉丁美洲”、“易卜生在英国”、“卡夫卡在德国”的例子不胜枚举。卡萨诺瓦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表面看起来是“民族的”、“独立的”、“纯文学性”的文学背后的各种美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价值交换。卡萨诺瓦的理论方法也可以被借用来思考德国—日本—中国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的德文藏书。本文将文学研究的场域锁定在“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和世界文学文库的出版——这一特定的对象上,进而提出“世界文学”空间的概念,将德国世界文学史和文库的诞生、流转看作一个具有时空特性的整体空间,并考察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对这一空间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德文语境里的“世界文学史”之所以收录各国的民族文学,部分原因在于19世纪中叶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德意志帝国即将统一的政治冲动。在鲁迅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诞生之前,德语的“世界文学”是指“日耳曼地区文学”。德文“世界文学史”和出版资本策动下大量发行的文库共同构筑了可以重新界定帝国文化身份的“世界文学”。这一“世界文学”有其自身的“中心”和“边缘”,“中心”无疑是德国,而疆域主要是日耳曼地区,它和世界的政治版图相关,但并非完全吻合。流通到东亚以后,这一“世界文学”的“中心”和“边缘”发生了偏移,形成了鲁迅“弱小民族的文学”中新的“中心”和“边缘”。“世界文学”在这一系列时空中建构和位移、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中诞生与流通,形成了一个流动的“世界文学”空间。通过对鲁迅德文书籍中的“世界文学”空间的探讨,本文希望在德国—日本—中国的跨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鲁迅“弱小民族的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关系。

3. 1867年瑞克阑姆万有文库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歌德的《浮士德》
一、在日本读德文书
增田涉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询问过鲁迅,如果能再到日本,他希望去什么地方看看。鲁迅回答说,希望上东京的丸善去看看。增田涉说这是因为鲁迅在日本的时候,经常去丸善书店,从那里吸收了“世界的文学和美术的知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还从丸善书店邮购书刊⑥。增田涉的回忆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留日时期的鲁迅是通过日本文学的中介吸收“世界的文学和美术的知识”。然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从丸善书店订购的多为德文书籍。
1906年春天,从医学院退学的鲁迅再次回到东京,决定专心学习外语,并将学籍放在“独逸语协会”所设立的独逸语学校内。鲁迅这时学习的不再是日语,而是德文;想从事的也不再是医学,而是文学。鲁迅在东京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依靠字典自己阅读,通过德文这块“敲门砖”去阅读“弱小民族的文学”,具体而言,就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以及俄国的文学⑦。据周作人介绍,这些“弱小民族”的作品英译本非常稀少,当时只有一些德文译本,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就有不少种。东京的书店因为觉得没有销路,便不销售,鲁迅只能列出书单,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再等待两三个月后由欧洲寄来⑧。
1868年由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兼朋友早矢仕有的(1837—1901)创立的丸善书店几乎垄断了战前日本的进口图书市场,承担着向近代日本读者传送“西方”知识的使命。当时的丸善书店是周作人所提到的德国瑞克阑姆出版社向日本出口图书的经销商⑨。
20世纪初的东京之所以能如此便利地阅读到德语书籍,无疑和近代日本存在一定规模的读者群有关。明治以后的日本在医学、自然科学、工程、农业等方面都开始向德国学习。东京帝国大学以及第一高等学校为德语书籍培养了一大批精英读者。以医学为专业的鲁迅自然会接触到德语,在仙台医专所学“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用腊丁、独乙”⑩。学习其他诸如法律、政治、农业、生物等学科也都要借助德语书籍。日本在彼时往往被看作是西洋文明和文化向东方传播过程中的转译者。而不满足于阅读日文书籍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多都会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在日本读“西洋书”或是像陶晶孙那样在日本研究欧洲文学。从丸善书店订购的德文书籍便成为鲁迅吸收世界文学和美术的中介。可以说,鲁迅乃至和鲁迅有相似经历的郭沫若、陶晶孙之所以能由医学转而进入文学,在日本销售的德语书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鲁迅在日本能够读到的德语文学书籍又有哪些呢?

4. 登载于1868年2月4日《莱比锡报》上的万有文库的第一张广告
二、 帝国统一背景下的“世界文学史”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曾有两部德文的《文学通史》给予周氏兄弟很大的帮助,“一部是三册本,凯尔沛来斯著,鲁迅所译《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即取材于此”;另一部是一厚册,“大概著者是谢来耳吧。这些里边有些难得的相片,如波兰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装的裴彖飞都是在别处没有看到过的”{11}。周作人所说的凯尔沛来斯(Gustav Karpeles)的三卷本《文学通史》,即1901年出版的三卷本《文学通史:从开始到当代》(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e, von ihren Anfangen bis auf die Gegenwart)。而周作人提到的另一部谢来耳(Johannes Scherr)著的一厚册的《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e),自1848年德国斯图加特首次出版后不断再版,1869年普法战争前夕第三次印刷时书的内容有所增加,推出了上下两卷本。然而,如果检索鲁迅的外文藏书,会发现其中并没有谢来耳所著的《文学通史》一书,而是保存着谢来耳的另一本名为《世界文学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的书{12}。事实上,在1900年,为了庆祝谢来耳1886年去世后出版的第九版《文学通史》发行量超过五万册,推出的第十版纪念版更名为《世界文学图史》{13}。鲁迅购买的即是这《文学通史》的第十版,也即《世界文学图史》(以下讨论仍沿用《文学通史》)。
“世界文学”的理念在德国可以追溯到歌德,但“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在德国却要迟至19世纪下半叶,即谢来耳和凯尔沛来斯生活的时期,他们是主要的“世界文学”史家。凯尔沛来斯是一位犹太文学史家。他在建构“世界文学”图景时,考虑更多的是收集欧洲犹太作家的作品,希望以此建构欧洲或世界文学史{14}。犹太作家与世界文学史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此不展开论述,本文主要讨论较能代表19世纪“世界文学”的德国性格的谢来耳的《文学通史》。从该书的不断再版就可以看出谢来耳的影响力及其在德国的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817年出生于符腾堡的谢来耳在1848年德意志革命时期提倡激进的共和联邦制,此后的大部分时间流亡于瑞士。他的文学研究大部分是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展开的。和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不同,谢来耳的《文学通史》不再强调欧洲或世界的文学的交汇,而是强调将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按时间顺序综合总括起来{15}。换言之,谢来耳的“世界文学”意味着由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学累加而成的“世界的文学”{16}。“世界文学”中的“世界”在19世纪的法国常常用“比较”(comparaison)来表达,而在德国则往往使用“总体”(allgemeine),该词强调的正是文学史编撰和材料收集上所采用的综合的方法{17}。这一总括性的总体文学观念与同一时期黑格尔哲学中的总体思想很接近。
谢来耳是怎样综合和归纳“世界文学”的呢?他的《文学通史》将世界划分为东方、罗曼语地区和日耳曼地区。该书下卷“日耳曼地区”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北美、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波兰、俄罗斯。在谢来耳看来,英国文学的根本精神无非是日耳曼精神{18}。也就是说,在以谢来耳的著作为代表的德语世界文学史中,有一个基于日耳曼语系的文化圈,该区域内的文学构成了德国“世界文学”的重要视野。这便是英国文学史里不曾出现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以在以谢来耳为代表的德语世界文学史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观点也非仅限于谢来耳。1887年德国文学史家里奥·伯格在解释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德国为何受欢迎时,就将其归结于德国与挪威共享的“日耳曼精神”,因此只有德国人才能理解“娜拉”{19}。德国19世纪的历史、法学研究也有类似的强调基于文化和语言所形成的日耳曼区域的倾向{20}。
事实上,除了书写世界文学史,谢来耳还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他是德国文化史的开创人之一。同一时期,他的另一部著作《日耳曼尼亚:德意志民族两千年》(Germania: Zwei Jahrtausende deutschen Lebens, 1879)便是在日耳曼文化绵延的历史背景中讨论德意志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谢来耳认为,不仅是德国,日耳曼文化圈内的其他民族文学也都共享着日耳曼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例如,冰岛的诗歌描绘了日耳曼地区信奉基督前的社会风貌,产生了北欧英雄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久远的北欧史诗发生了转变,发展出独自的传统{21}。在谢来耳看来,在共同的日耳曼文化传统里,不同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的民族文学。这些民族文学共享着同一个原始文化记忆。
谢来耳写作这些历史与文学史著作的一大背景便是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22}。作为符腾堡地区民主党的代表,谢来耳希望建立一个共和联邦制的德意志。共和理想失败后,谢来耳流亡瑞士。此时,文学和历史研究更成为一种表达他的政治理想的途径。早在1844年,谢来耳就曾写道:“我们德意志民族除了文学没有任何公共生活。我们的行为结果也只有文学。”{23}在政治运动较为落后的德国,像谢来耳那样的共和人士将文学看作是替代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没有政治的公共生活,所以只能创造出一个文学的公共空间{24}。基于谢来耳的共和联邦制的理想,其文学史中有着矛盾的两面:一方面,占有重要位置的是海涅、拜伦、彭斯、雪莱、密茨凯维支、普希金等具有反抗意识或民族意识的“民族诗人”;另一方面,其历史著作也体现出对于各个民族共同的日耳曼文化源头的迷恋,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联盟的冲动。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总体文学、日耳曼文化圈内各个民族的文学并非不分伯仲。对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谢来耳承认其在文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但认为他无法和德国诗人媲美。与德国的歌德、席勒和莱辛相比,莎士比亚只能体现出16、17世纪英国文明的局限性{25}。相反,虽然德意志民族的民谣并不见得比北欧的史诗和苏格兰的民谣优秀,但德意志民族具有比其他民族都优越的特点,那就是“普世性”(universalit?覿t){26}。这种普世性即是谢来耳对德意志民族文学,也是对其自身的世界文学史的定位。就在1848年,谢来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画廊》,即日后《文学通史》的雏形。他不无自豪地说“这样的书只有在德国才有可能。因为,德国精神的普世性以及德国科学的不懈追求精神可以很好地理解全部民族、所有时代的思想产物,没有任何民族可以企及”,“我们德意志民族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世界文学的拥有者(Besizter)”{27}。此后不断再版的《文学通史》也一再强调,在所有民族中,德意志最具备聆听“世界文学”语言的“全球接受能力”(die universelle Empfaenglichkeit){28}。借此,谢来尔暗示德国以及德语在“世界文学”中的超群地位。这种言论正契合了半个世纪前费希特对德国人所作的那场著名的发言《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其中就有德意志民族总能很好地理解其他民族,甚至比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更准确这样的言论。而半个世纪后出版的《文学通史》也预示着俾斯麦时代之后“世界政策”(weltpolitik)时代的到来{29}。
可以说,谢来耳的《文学通史》兼有佩里·安德森所称的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特点。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也曾在其《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指出,到19世纪中叶为止,德国已经在反对拿破仑的进程中发展出了一套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如葡萄藤那样,缠绕在不断延伸出去的世界主义的藤架之上”。在长时期对法国的挫败感中催生了德意志对欧洲和世界的认同,并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特性的一部分{30}。具体而言,就是像安德森所说的那样,基于民族主义的德国通过承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创造出一种“修正的普世主义”{31}。通过谢来耳的《文学通史》我们看到,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安德森所说的“修正的普世主义”又被进一步强化为民族优越性的一部分,甚至和帝国的建立拥有相同的政治理想。此时的“世界文学”已不具备歌德时期的历史人文主义因素,只代表各民族文学的集合,而德国则是“被上帝选中”的各民族文化的中介和集大成者{3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德国最初的世界文学史应运而生了。谢来耳《文学通史》中的民族文学理想离鲁迅后来的“弱小民族的文学”概念似乎非常遥远。

5.johannese scherr
三、 资本主义的逻辑
伴随着德国“世界文学”崛起一并出现的正是德国蓬勃的出版业。浩瀚的“世界文学”以“文集”、“文库”、“选本”的形式出现在书架上。正是在1867年,即谢来耳《文学通史》重版前的两年,为了满足市场对文学的需求,对鲁迅而言意义重大的“瑞克阑姆小文库”正式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万有文库”(Universal?鄄Bibliothek),也即鲁迅自己所称的“莱克郎氏万有文库”。鲁迅从丸善书店购买的德文文学书籍主要来自这一丛书。“万有文库”出版了许多文学作品,以1905年为例,丸善书店出售的“万有文库”有八十三种,其中包括歌德、希勒、卢梭的文集,也包括诸如高尔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俄国文学作品。到周氏兄弟出版《域外小说集》的1909年,丸善书店出售的“万有文库”已达到了二百八十九种,其中就包括许多德国及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33}。
“万有文库”起初主要出版古典作品。这个始于1867年的文库得以成立,多亏了1867年11月实行的北德意志联邦法。该法律规定作家身后三十年,其版权归属公共领域,出版时无须向作家及任何出版社缴纳版税。在这一新法律改定的背后是德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自我定位,以及希望通过古典文学普及国民教育、建立文化身份的政治意图{34}。早在1852年,谢来耳就通过出版《德国文化风俗史》(Deutsche Kultur?鄄und Sittengeschichte)来表达他的文化大国理论,声称德意志的边界并非是由政治任意划定的,而是由文化、教育、语言、思考方式、风俗自然形成的{35}。长期和德国处于竞争地位的英、法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军事和政治运动,与此相对,谢来耳提出德国文明的基础是文化。在18世纪下半叶倡导文化是保证德意志统一、战胜政治分裂的一种方式{36};一个世纪以后,再次强调文化则是德意志民族对长期处于法国阴影下的民族身份的一次张扬。谢来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先于德意志帝国的疆域统一提出了文化统一的概念,而敏锐的出版资本则紧跟其后,在出版法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建立了一个通过阅读构建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
除了“万有文库”,鲁迅还收集其他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1906年,鲁迅曾开列出一个《拟购德文书目》,分别向柏林的希尔格出版社(H. Hillger Verlage),莱比锡的格辛出版社(Goeschen’sche Verlagshandlung)、托伊布纳出版社(B.G. Teubner)、克维勒和迈耶出版社(Quelle und Meyer)以及哈勒的奥托·亨德尔出版社(Otto Hendel)求购各类图书{37}。格辛出版社有“格辛文集系列”(Goeschen Sammlung);奥托·亨德尔出版社则有“国内外总体文学文库”(Bibliothek der Gesamtt?鄄Literature des In?鄄und Auslandes,1886—1915),这是一套专门出版各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丛书,1886年至1915年间共出版了两千五百七十三种不同的文学书籍{38}。从该丛书所标榜的“总体”来看,沿袭的也是“综合”的思路。鲁迅买到了《拟购德文书目》中列出的许多书,其中就包括奥托·亨德尔出版社“国内外总体文学文库”中所收的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Leonid N. Andreev)的《深渊及其他小说》(Der Abgrund und andere Novellen)、魏斯(Albert Weiss)所著的《波兰中篇小说》(Polnisches Novellenbuch)和《波兰诗歌》(Polnische Dichtung in deutschem Gewande)、匈牙利作家厄特伏斯(József E?觟tv?觟s)的《乡村公证人》(Der Dorfnotar) 等。这最后一本书,鲁迅收藏了瑞克阑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和奥托·亨德尔出版社“国内外总体文学文库”两个版本{39}。“万有文库”以其漂亮的封面、便宜的价格、优质的纸张、不删减内容等优势成为了文库本的领头羊。它在德国的售价是每本二十芬尼。据周作人介绍,在日本购买时每册一角至五角,是穷学生也负担得起的价格{40}。据统计,鲁迅在日期间购读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书籍共有五十种,全部是德译本,其中瑞克阑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就占了三十五种{41}。而从现有藏书来看,在包括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作家在内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德文书中,“万有文库”多达七十多本,占一半以上,而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文学则除了少数的几本外全部购自“万有文库”{42}。
鲁迅的藏书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万有文库”的出版策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版发行德国以外的外国作家作品成了瑞克阑姆出版社的一项重要举措,早期的重点是北欧作家和俄国文学。北欧文学的德语译本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作家的作品相继发行。19世纪80年代又开始出版俄国文学的德语译本,先后发行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作品{43}。1930年,鲁迅从日文《戈理基全集》第七卷译出高尔基的《恶魔》时就曾提到他所阅读的一个更早的“万有文库”版本{44}。事实上,从1901年到1906年,“万有文库”共出版了六种高尔基的作品,鲁迅全部购齐{45}。
为何“万有文库”会愿意出版“弱小民族的文学”呢?这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在19世纪末,原本处于经济、地缘政治边缘的北欧一跃成为了一个文学重心,诞生了像易卜生和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那样世界闻名的作家{46}。易卜生的剧本在酷爱戏剧的德国深受喜爱,这自然有上文提到的日耳曼文化圈的因素。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统一的出版联盟“伯恩公约”(Berne Convention)始于1886年,但是挪威直到1896年才加入,丹麦于1903年、瑞典于1904年才加入,而俄国则一直没有加入。这就意味着瑞克阑姆出版社不必为出版俄国和北欧作家的作品额外支付版税。在挪威加入版税联盟时,“万有文库”已通过无版权的形式出版了十七部易卜生的作品{47}。1900年当年在销的易卜生作品就有十九种,印数高达一百四十万册{48}。到1917年为止,易卜生成为瑞克阑姆出版社最畅销的外国作家,印数高达四百五十万册,远超第二位的莎士比亚{49}。“弱小民族的文学”能够进入德国文库,并非只是文学自身的价值在起作用,除了日耳曼文化圈的因素外,至少还部分地取决于资本的法则。无论如何,正是被翻译成德语、进入德语世界文学史并被“万有文库”选中以后,它们才有机会在欧洲乃至东亚被广泛阅读。

6. 明治40年(1907)年左右京都的丸善书店
四、 “世界文学”的转换与再生
卡萨诺瓦在论及拉丁美洲作家超越时空差异、获得全球认可时称,文学对于民族的原初性依附是造成文学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当人们在世界结构中为民族文学空间明确定位以后才能找到它们真正的价值。而拉丁美洲文学在全球政治空间中所获得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显然很不相称{50}。相似的说法或许可以赋予那些出现在德国世界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这些民族文学通过进入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和各种“文库”获得了在文学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这里存在着一个“世界文学”空间的等级结构。正如谢来耳所说,文学是德国唯一的公共空间,对于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德国,文学和文化是重塑民族身份的重要途径。而刚刚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德国需要通过向世界重新界定和解释何为“世界文学”来创造一个德国赖以称霸的文学世界。178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还在为和邻居法国相比德国没有一个令人骄傲的文学空间而惭愧{51}。一百年之后,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家和出版资本联手创造了一个“世界文学”的文学空间。而用以重新界定“世界文学”的部分资源便是和德国相比处于政治、经济结构弱势的东欧、北欧等日耳曼地区的民族文学。通过对来自外部空间的文本的“认证”,一个德国的“世界文学”的文学空间被创造出来,而这种由文学和文化表述的政治理想和在实际政治、军事领域里展开的帝国冲动并不相悖。毫无疑问,德国的“世界文学”空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19世纪德意志帝国建立前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使德国的“世界文学”空间得以在现实世界中构造起来的是德国出版业的发展,是看准读书市场、对利润有着不断追求的瑞克阑姆出版社。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世界文学”的产生很重要的条件便是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的世界市场的出现,德国的“世界文学”得以从物质层面充实起来要依赖于出版资本的全球化{52}。雄心勃勃的瑞克阑姆出版社很快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消费。鲁迅留学所在的日本一直是瑞克阑姆出版社重要的海外销售市场。1914年,瑞克阑姆出版社向东京派驻了一位专职销售人员,这也是这家出版社首次向海外派驻销售人员。该年瑞克阑姆出版社在日的销量是三万册{53}。
正如以上的讨论所揭示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资本、理论和政治力量三者齐头并进。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在帝国统一之前就在理论上践行了帝国的“世界文学”观。虽然谢来耳追求的是共和联邦制而非德国后来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在追述共同的日耳曼文化、构建普世性和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方面,谢来耳和帝国的施政者有着相同的目标。而出版资本又进一步使得“世界文学”空间得以在全球消费和流通。就连远在东亚的日本和中国都成为德国“世界文学”的接受者和消费者。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伴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资本的流通,“世界文学”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家间也产生了多种意义。“世界文学”既不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经典,也并非像谢来耳所描绘的那样是全部作品静止的排列与累加,更不应该是“世界”在历史性、社会学或者地理上的附属品。鲁迅通过德文书籍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一概念的新的可能。德国的“世界文学”自然有其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有其民族主义的追求、帝国统一的文化诉求、图书生产与流通的资本力量,然而一旦德国的文库与世界文学史通过日本流到中国,“世界文学”就从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语境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之中。“万有文库”不仅滋养了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木下杢太郎、柳田国男等一大批日本作家,而且滋养了留日期间的鲁迅,孕育了后来的“弱小民族的文学”。我们看到谢来耳的世界文学史为20世纪初身在日本的鲁迅探寻另一个不以英、法强权为中心的、被边缘化的、主要由弱小民族组成的“世界文学”提供了物质可能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谢来耳“世界文学”史观的影响是一个有待继续考察的问题。谢来耳对于物质主义的反感,对于拜伦、密茨凯维支与裴多菲的喜爱,对于文学的政治功用的认识,这些都能在鲁迅早期文言论文里找到影子,只是鲁迅没有在文章中直接提到过谢来耳。北冈正子在对《摩罗诗力说》材料源进行追踪时也只是简单地谈到了鲁迅曾参考谢来耳的“世界文学史”{54}。至于鲁迅是如何参考并将谢来耳《文学通史》中的“日耳曼地区文学”进一步转换成其“弱小民族的文学”还有待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19世纪下半叶继歌德之后的德国的“世界文学”空间构成了鲁迅早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鲁迅回国后的20世纪20年代持续发挥作用。德国“世界文学”空间进入鲁迅的视野并转变为“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世界文学”从一种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文本叠加向丹穆若什所说的“一种流通和阅读模式”的转换{55}。不可否认它的产生与流通受制于欧洲中心和世界边缘的全球结构,然而它的流通和阅读也在世界各地生产出企图与原有的不平等的世界结构相抗衡的力量。
①② 戈宝权:《鲁迅与世界文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③⑦⑧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第41—42页,第42页。
④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says by Patrick Han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0.
⑤{36}{50}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5—389页,第39页,第40页。
⑥ 增田涉:《我的恩师鲁迅先生》,武德运编《外国友人忆鲁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⑨{33}{53} Regine Mathias, “Reclam in Japan. Universal?鄄Bibliothek und Iwanami?鄄Bunko”, in Dietrich Bode (Hsg.), Reclam, 125 Jahre Universal?鄄Bibliothek 1867-1992, Stuttgart: Reclam, 1992, S. 259, S. 260, S. 260.
⑩ 鲁迅:《041008致蒋抑卮》,《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11}{4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第327—328页。
{12} 事实上,《世界文学图史》的目录与《文学通史》完全一致。
{13} Otto Haggermacher, “Vorwort zur neunten und zehnten Auflage”, in Johannes Scherr,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Vol. 1, Stuttgart: Franck’sche Verlagshandlung, 1900, S. vii.
{14} Johannes Sabel, Die Geburt der Literatur aus der Aggada: Formationen eines deutsch?鄄jüdischen Literaturparadigmas,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S. 84.
{15}{21}{28} Johannes Scherr,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Franckh, 1851, S. iv, S. 327, S. iii.
{16}{17} Theo D’haen,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6, p. 17.
{18} Johannes Scher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Otto Wigand, 1865, S. xff.
{19} Leo Berg, Henrik Ibsen und das Germanenthum in der modernen Literatur, Berlin: Eckstein, 1887, S. 4-5.
{20} Heinz Gollwitzer, “zum politischen German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in Josef Fleckenstein (Hsg.), Festschrift fuer Hermann Heimpel zum 70. Geburtstagam 19. September 1971, Bd.1, G?觟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71, S. 282-356.
{22} Cf. Johannes Scherr,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Vol. 1, S. v.
{23} Johannes Scherr, Poeten der Jetztzeit in Briefen an eine Frau, Stuttgart: Franckh, 1844, S. 124.
{24} Peter Uwe Hohendahl,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8.
{25} Johannes Scher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82, pp. 83-84.
{26}{35} Johannes Scherr, Deutsche Kultur?鄄und Sittengeschichte, Leipzig: Otto Wigand, 1882, S. 247, S. 4.
{27} Johannes Scherr, Bildersaal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Becker, 1848, S. vi.
{29} Michael Boyden, “Why the World is Never Enough: Re?鄄conceptualizing world Literature as a Self?鄄Substitutive Order”, in Nele Bemong, Mirjam Truwant & Pieter Vermeulen (eds.), Re?鄄thinking Europe: Literature and (Trans) national Identity, Amsterdam: Rodopi, 2008, pp. 70-71.
{30}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6页。
{31} Perry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No. 14 (2002): 9.
{32} John David Pize, “Nationalism and revival weltliterature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in 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7-68.
{34} Peter Uwe Hohendahl, Literarische Kultur im Zeitalter des Liberalismus 1830-1870, München: C.H. Beck, 1985, S. 289-302.
{37} 鲁迅:《拟购德文书目》,刘云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4页。
{38} Mark W. Rectanus, Literary Ser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om 1960 to 1980,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4, S. 41-42.
{39}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西文书目》第3卷,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版,第42页。
{41} 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上,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
{42} 根据鲁迅外文藏书《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整理。
{43} Georg J?覿ger, “Reclams Universal?鄄Bibliothek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Erfolgsfaktoren der Programmpolitik”, in Dietrich Bode (Hsg.). Reclam, 125 Jahre Universal?鄄Bibliothek. 1867-1992, S. 34.
{44} 鲁迅:《〈恶魔〉译后附记》,载《北新》1929年第1、2期合刊特大号。
{45} Eberhand Reissner,“Die Universal?鄄Bibliothek als Wegbereiter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e in Deutschland”, in Dietrich Bode (Hsg.), Reclam, 125 Jahre Universal?鄄Bibliothek.1867-1992, S. 130.
{46} 鲁迅挪威文学的藏书也主要集中在易卜生和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两位作家。
{47} 参见瑞克阑姆出版社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reclam.de/info_pool/wir_ueber_uns。
{48}{49} Aldo Keel, “Reclam und der Norden: Autoren, titel, Auflagen 1869-1943”, in Dietrich Bode (ed.), Reclam, 125 Jahre Universal?鄄Bibliothek.1867-1992, S. 140, S. 145.
{51} FrederickII, King of Prussia, “Ue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ie Maengel, die man ihr vorwerfen kann; die Ursachen derselben und die Mittel, sie zu verbessern,” in Horst Steinmetz (Hsg.), Friedrich II, Koenig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Texte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Reclam, 1985, S. 60-69.
{5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54} 北岡正子『魯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 : 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第69頁。
{55}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作者熊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资料来源:文艺研究,2017年6月22日
http://mp.weixin.qq.com/s/qx4a-Jj49AKMKUFnIt6R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