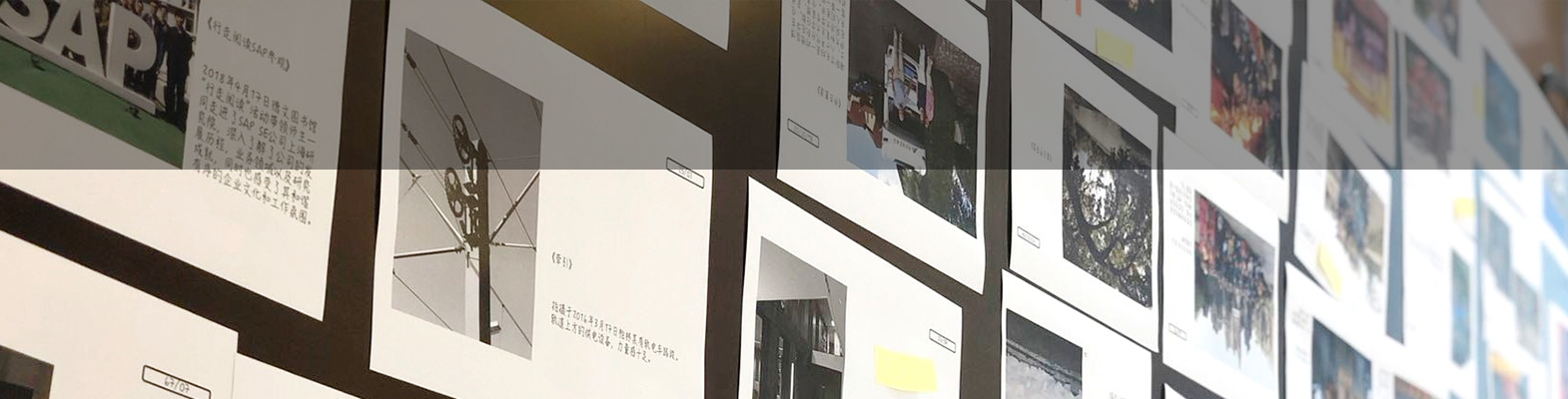主营儿童和青少年图书的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Beltz & Gelberg)于2021年庆祝建社50周年,旗下出版品牌Gulliver也迎来成立35周年的傲人里程碑,二者都属于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贝尔茨出版集团,集团是德国最重要的教育和心理学图书出版商之一。
对话人:
岳根·博思 |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
玛丽安娜·吕贝尔曼 | 贝尔茨出版集团总经理
佩特拉·阿伯斯 | Beltz & Gelberg 和 Gulliver 出版总监
弗兰齐斯卡·希贝 | 营销和销售总监
Q 博思: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成立50周年及旗下出版品牌Gulliver成立35周年都时逢新冠疫情蔓延的次年夏天。您对此有何感想?周年庆计划完成了吗?
吕贝尔曼:我们倾向于从整个贝尔茨出版集团的视角来看,已经有180年的历史了,但见证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也令人感到欣喜——这是180年来最大的创举,为集团带来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收益。
阿伯斯:在疫情背景下,我们显然无法与旗下所有作家一起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得想办法做到既能有一些关注度,又能让人们保持安全距离。于是,“周年庆巴士”的点子应运而生——在全国巡演,中途去看看我们的作家和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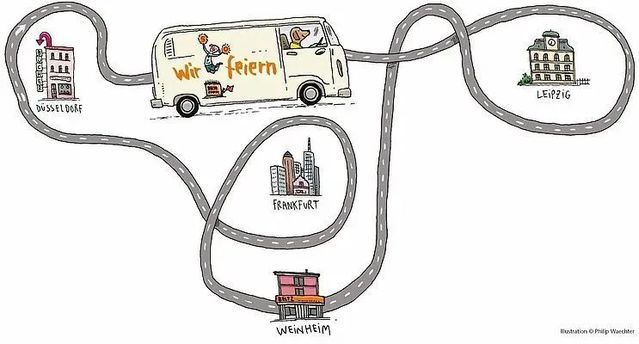
Q 博思:回首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早年的岁月,童书出版起初对于出版社而言不是常态吧?
阿伯斯:也不是,毕竟当时不是简单地创立一家童书出版社,而是在已有印刷厂的背景下,加上教育出版的迅速发展,这样的延申其实很合乎逻辑。
吕贝尔曼: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始于我父亲曼弗雷德·贝尔茨-吕贝尔曼(Dr. Manfred Beltz-Rübelmann)和汉斯-约阿希姆·盖尔伯格(Hans-Joachim Gelberg)在书展上的一次愉快邂逅。盖尔伯格先生找到我父亲,提出他有一些点子。我父亲乐于开展新项目——这也是后来集团又增加了心理学出版项目的原由,他在另一次书展上遇到了弗兰克·施沃雷尔(Frank Schwoerer,Campus Verlag曾经的出版人),并就此展开合作。他们的合作模式为:一方提供资金,另一方提供点子,从而形成合作多年的默契团队。
博思:书展上的一次偶遇带来了深远影响……
吕贝尔曼:是的,加上我父亲对发展公司有着全面的兴趣——推动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在财务和业务方面的发展。
Q 博思:橙色商标是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的鲜明标识,它是怎么产生的?
吕贝尔曼:在那个年代,图书的配色都十分鲜明。盖尔伯格想设立一个含主题的标识,我父亲也很支持。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为儿童和青少年出版教育类书籍。几周前,我在档案馆里发现了一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书,也是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但它时至今日都很适合再版。
阿伯斯:盖尔伯格从事过图书贸易,了解业务,具有远见,知道该如何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博思:想到生态学、性教育等主题时,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阿伯斯:盖尔伯格有文学背景。他总是说,如果你可以为成人写作,那也可以为儿童写作。他对所有的作家都这么说过。同时社会也为这些话题做好了准备。他对非文学作品不太感兴趣,但在文学作品中融入纪实主题,这样的作家有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linger)、莱奥妮·奥索斯基(Leonie Ossowski)等。
博思:传记曾是青少年图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伯斯:是的,我们推出传记系列的灵感源于纳粹焚书事件,想要“复活”那些作者的生平和文本。盖尔伯格的做法相当务实:他只出版已逝人物的传记,这样就可以避免版权问题。这个系列为平装本,小篇幅——因为这些书需要让大量读者能够买得起。
Q 博思:这些都是德语作品吗,还是也有一些翻译著作?
阿伯斯:还没有译著,盖尔伯格专注于德语文学。后来还是通过与他合作的编辑才做了译著。他重视叙事类童书及图画书。正是他挖掘了作家尼古拉斯·海德巴赫(Nikolaus Heidelbach),给了他展示的机会——一个游走于成人书和童书之间的人。
Q 博思:反过来看,这些书在国际上受欢迎吗?
阿伯斯:人们早就对雅诺什(Janosch)和米亚姆·普莱斯勒(Mirjam Pressler)的作品感兴趣了。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海外出售版权。现在也有能力继续拓展版权业务。版权大量销往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在俄罗斯也数量可观,当然,还有韩国。我们切实感受到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目前销量再度回暖。此外,在土耳其也售出了不少版权,尤其是雅诺什等畅销作家的作品。这既与各国的开放程度有关,也需要首先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博思:您成功地把许多作家的作品变成了经典,这很了不起。
吕贝尔曼:这也许也是因为我们旗下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至今仍然作为学生读本。
阿伯斯:是的,这也是我们出版社的一个特色:我们长期持有版权。而今这难度越来越大了,因为每年必须卖出一定数量的书,才能使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回本。我们无法再持有彼得·彼特·赫尔特林(Peter Härtling)或克劳斯·科登(Klaus Kordon)每本书的版权,但在交出版权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跟作家埃尔温·莫泽尔(Erwin Moser)有非常好的合作。莫泽尔曾经很受欢迎,之后更多作家后来居上,莫泽尔又因病无法完成新作品,于是他的书开始打折。但我们设法重建他的高关注度,重新编辑他的作品,因为他的故事太有深度了。他的书几乎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这代人记得他并也开始为人父母。从雅诺什和莫泽尔身上,我们看到:需要有耐心,然后判断时机正确与否。对莫泽尔来说,现在就是时机,因为他足够镇静,知道如何以小见大。
Q 博思: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很好。所以您更像是一个代理人,与作家们一起工作,助推他们。您也把莫泽尔的作品版权卖到国外吗?
阿伯斯:是的,有很多,而且很快就会销往日本了。他作品中的视觉语言、那些极简的线条,都很契合日本文化。
Q 博思:与作家长期合作是典型的德国出版社特质,还是只是贝尔茨出版社的特质?
吕贝尔曼:我们当然乐于把一些东西留在身边,比如人、作家。我们既想和他们携手“走出去”,也想扮演好守护者的角色。
阿伯斯:对于其他长时间运营的童书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年限尚短的出版社还没有存书,他们可能甚至没有机会与作家和插画家建立稳定的关系,因为作家和插画家如今都同时与许多不同的出版社合作。
Q 博思: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出版社的忠诚度不够?
阿伯斯: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连我们都感觉到:让插画家只和我们合作越来越不容易了。如果我们能够与作家和插画家共同创造出一些独一无二的作品——一些只有贝尔茨&盖尔伯格出版社才能实现的东西,那已经算大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做得相当好。
博思:让作家拥有较高的声誉总是好的。
希贝:是的,这样在市场上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点。
阿伯斯:插画家阿克塞尔·舍夫勒(Axel Scheffler)就是如此。他本人也这么认为。
Q 博思:当您回顾贝尔茨出版集团走过的这180年,您觉得如何平衡好传统和创新呢?
吕贝尔曼:我觉得拥有传统很好,这样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创新和展望。出版社已经经历并克服了那么多困难,让我们多了份沉着,能够镇定自若地工作。我们所真正看重的是这些年来始终坚持的独立性。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让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接触公司业务,因为我们不想成为只坐在桌旁拍板的老合伙人。我们不会分割家族企业,并鼓励大家参与进来,当然这也不是义务。我们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保障出版社的独立,甚至是七代出版人的独立。
Q 博思:新冠疫情推动了数字化,在学校里尤为明显。这对公司战略有何影响?App仍然是您感兴趣的领域吗?
希贝:我们的App(比如阅读及拼写训练软件Wörterfresser)是王牌项目。我们常说:阅读和大声朗读当然有情感层面,是我们所关注的。相比童书,其他出版领域的数字化压力要大得多。新冠疫情期间,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儿童故事书特别依赖于书商的推荐,我们必须努力弥补这一点,不论是通过社交媒体,或是通过技术层面来优化搜索引擎等。
Q 博思:您觉得播客有帮助吗?
希贝:在疫情期间,我们开设了播客频道,因为我们知道此前的推广平台会减少,并且想向读者推荐我们的作家。播客从业者都知道:如果没有真正的大咖,要做出名堂来有多难。事实上,播客50%的预算都花在了营销上。
阿伯斯:疫情让我们的目标受众走向数字化。例如,由于居家上网课,父母买书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这方面的连锁反应我们必须充分考虑。问题不在于内容有多好,而在于我们此前只以图书为载体的内容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或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哪些年龄段、哪些家长和老师对特定类型的内容感兴趣?我们比在2018年预想的要更快面临这些问题。
Q 博思:我们来聊聊故事。儿童音频播放器Toniebox在整个欧洲都很成功——这类事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特有的触感和感觉。您也把版权卖给Tonie了吗?
阿伯斯:是的,马丁·巴兹塞特(Martin Baltscheit)的《狮子的故事》(Geschichten vom Löwen)是Tonie的第一个播放盒玩偶形象,所以我们也算有间接参与。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创意,但大家都以传统图书业的傲慢视角出发,低估了它。以前,如果一本畅销书被另一家出版社拿下,一定很让人懊恼。而如今其他的形式也得跟上。我们很快就推出了《猫武士》(Warrior Cats)系列及其有声读物。这一投入很值得,我们很快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做这类决定动作要迅速,我们以前犹豫得太久了。
Q 博思:您之前提到一本70年代做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书。如今推出的“100%自然图书”系列是否也为您带来了经济回报?
吕贝尔曼: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印刷厂或出版社“漂绿”(以某些行为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通过资质“买断”版权,最终却扔掉成千上万还裹着塑封的书。我们有在德国巴特朗根萨尔察的印刷业务资质,并为此付了一大笔钱,但这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量少用电力和化学品。使用绿色电力是有益的,也是我们所践行的。但出版商仍在采用化学方法制作更能吸引消费者的书籍,例如覆膜——这是我们必须做出改变的地方。我们确实在考虑如何以最环保的方式生产每一件产品。
阿伯斯:问题也在于我们生产的比卖出的多,因为我们必须为书店和书商维持一定水平的库存,而这些库存最终可能滞销。这意味着总是有一定的回报率。按需印刷是不可行的。100%自然图书系列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因为我们售出了很多版权,也有合作出版,因此可以大量印刷。
博思:事实证明推出这个系列是正确的选择。
阿伯斯:这一系列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顾客得愿意为此花更多的钱。人们想要的和他们愿意付出的有时相差甚远。我们有相对购买力强的客户,但他们也会在意价格。
博思:我相信读者会愿意为了高质量而花更多的钱。
希贝:童书有一定的价格限制,比如一份传统的生日礼物售价不应超过10欧元——这也是学校书籍的价格上限。但是,整个图书业终于要开始提价了。
博思:出版社位于身份认同和多样性政策的前沿,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经验。
阿伯斯:这是一个大话题。我们仔细研读每本书,但不会将经典作品“现代化”。有一个关于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linger)的例子。我和她的女儿们讨论后一致认为:涅斯特林格本人不会想对章节进行修改,于是我们就照原样出版了。后来,这就不再是问题了。前不久有个例子是:在雅诺什的作品中,主角的爪子放在了女性胸部上,我们也没有进行改动。我们不仅关注文本,也关注图像。因为插画家也必须学会展示多样性,不能只是单纯给同一张脸换个颜色。
Q 博思:您如何看待“敏感信息审查员”?
阿伯斯:我们有一本计划明年出版的书关于跨性别者。敏感信息审查员们提醒了我们一些十分关键而我们自己却没能发现的东西。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出版社手上——即使有时双方没能达成共识。
博思:非常感谢诸位接受此次访谈。
*注:以上访谈来自2022年法兰克福杂志(英文)
电子版下载地址:www.german-stories.de/german-stories-news-frankfurt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兰克福书展”,2022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