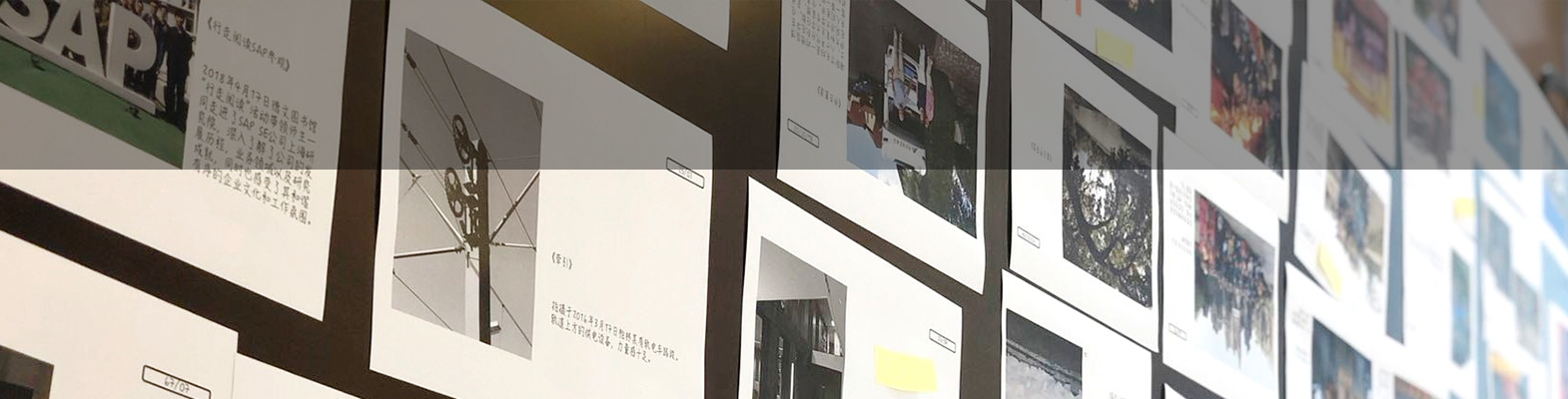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在文字间穿行”翻译家系列第一讲
匠心•学问•灵感 ——论文学翻译的三位一体
主讲人:黄燎宇(北京大学教授,德语系主任,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2017年6月10 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学津堂

根据黄燎宇老师讲稿整理,并经老师授权©文津阅读
匠心·学问·灵感
——论文学翻译的三位一体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谢谢国图的邀请。
我翻译做了二十几年,翻译课讲了十几年,最近几年也搞了一些翻译讲座和翻译工作坊。但今天这场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考验。过去讲翻译,面对的是会德语的,讲座的方式也很简单,拿中文德文一对照,几乎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今天我面对的是各界人士和各路高手,听众中间绝大多数不会业内人士所说的始发语,我的翻译始发语是德语。我感觉表达难度骤然加大。
为什么呢?都说译者是搬运工。他的工作就是从始发语把东西搬到目的语。现在来了一个译者,要向只懂目的语的众人诉说自己从始发语往目的语搬运东西是多么地不容易、是多么地了不起、又是多么有意思。这谈何容易!人家没去过你的始发地,没走过你的搬运路线,所以无从判断你的翻译路途是否真的遥远、是否真的凶险、是否真是风光迤逦。其结果,有可能是译者既说不出自己哪里辛苦,也说不出自己哪里有快乐、哪里很自豪。所以,我希望自己今天能把道理讲明白,把话说清楚。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为《匠心·学问·灵感——论文学翻译的三位一体》。演讲内容既涉及翻译理念——简称译理,又涉及训练翻译技巧——简称译技(欢迎大家发出笑声),更涉及译者的职业道德——简称译德。我演讲的目的,则是要展现翻译之重要、之艰难、之有趣。我承认,这一选题带有浓厚的行会意识,有点王伯卖瓜的意思。
翻译如何重要,大家已经听了不少。从宏观讲,翻译活动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众所周知,佛教的传播始于翻译;让西方世界陷入分裂的宗教改革的翻译离不开马丁·路德的翻译;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更是离不开翻译。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的历史始于1898年,当时叫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之后即1912年才更名北京大学。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大学的外国语学院的历史比北京大学还悠久一些,因为它把自身起源追溯到1862年清政府所创立的同文馆。结合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看,创立同文馆可以视为一项翻译兴国的举措。时至今日,翻译事业依然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不仅有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我们还有中央编译局,全称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这是我们国家人数最少、也最袖珍的部级单位之一。一个二、三十人的翻译团队需要一位部长来领导,这种重视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均属罕见。
但我今天不是来高谈阔论的,也不是来讲翻译理论的。我对脱离实践的翻译理论一向有看法,所以我喜欢在我的课堂传播一句业内名言:“会搞翻译的就埋头搞翻译,不会搞翻译的就讲翻译课,不会讲翻译课的就讲翻译理论”。下面我要讲的,都是点点滴滴的日常观察和日程体会。
讲翻译,通常都从词法和句法两个角度入手。词法讲词汇的翻译,句法讲句子的处理。从句法讲德译汉特别有意思,因为德汉的语言结构差别太大。但考虑多数人不会德语,我今天就专门谈词汇的翻译,尤其是专有名词和物体名称的翻译。而且是从翻译之憾即翻译留下的遗憾说起。根据常识或者说辩证法,人们总是失去什么才知道什么可贵。以此类推,错误的翻译最能让人意识到翻译之可贵。
我从乐天之憾讲起。
乐天就是路人皆知的韩国乐天集团。今天,乐天集团是十三亿中国人最熟悉、最厌恶的外国企业,乐天超市在中国人眼里最扎眼。乐天超市四处遭到民众的抵制。谁让这个乐天集团用美国的萨德系统点燃了正义的怒火?乐天的确咎由自取。因为萨德,我也讨厌乐天。但是我对乐天中国分支的看法比普通民众还要多,因为我是做翻译的,我对乐天的意见已经憋了好多年。对于我,乐天首先是个翻译问题。有人也许会问:乐天的翻译怎么可能招惹你?乐天的翻译跟你一个搞德语文学的、跟你一个做德语文学翻译的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太有关系了。
故事得从2011年说起。那年秋天,韩国的德语文学研究会邀请我赴韩参加在庆州举行的年会。路过首尔的时候,他们安排我下榻位于市中心的总统饭店。我在总统饭店周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座富丽堂皇的商厦,商厦的名称是我太熟悉不过的西文或者说德文:Lotte。这个字眼我太熟悉,所以我不敢认,甚至不敢相信。什么是Lotte?Lotte就是绿蒂!绿蒂就是夏绿蒂的简称、昵称!夏绿蒂就是最最有名的德国文学家沃尔夫冈·封·歌德的最最有名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女主人公!我们都知道,绿蒂是个可爱的姑娘,人见人爱。她是少年的维特的最爱,可怜的维特最后就是因为恋爱绿蒂不成而开枪自杀。歌德和绿蒂的故事流传了二百五十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欧洲人,亚洲人。我心爱的作家、号称“二十世纪的歌德”的托马斯·曼还写过一部题为《绿蒂在魏玛》的小说。这部小说有两个中译本:一个叫《歌德与绿蒂》,一个叫《绿蒂在魏玛》。我本人很喜欢这本小说,我还笔酣墨饱地写过一篇讨论这本小说的论文,讨论的出发点是小说中的一则号称来自中国的格言:“伟人乃公众之不幸”。
大家可以想象我在首尔发现这个名为Lotte的商厦是什么心情,是什么反应。没错,我马上向韩国同行求证。他们告诉我,这就是歌德的绿蒂。我认为他们在开玩笑,所以没当真,也没有继续研究。我相信自己把这个商厦名称跟绿蒂扯到一起纯属自作多情,纯属专业异化,说出去会让人笑话。另外,我不爱逛商店,也不关注商店的存在,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Lotte早已登陆中国,在中国搞起了好多分店。等萨德事件出来后,我才重新关注它,才启动对它的翻译调查。为此,我请一个会韩语的亲戚去乐天的韩语版官网查看其企业名称的来历,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下面是我的亲戚粗略翻译的文字说明:
乐天创始人辛格浩。20世纪40年代初,20岁出头的辛格浩前往日本勤工助学,一边送报纸送牛奶,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虽然生活很艰辛,他还是醉心于文学。看了德国文豪沃尔夫冈·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他深受感动,对于夏绿蒂这个大众情人尤其印象深刻。因此,辛格浩在1948年创建公司时取名Lotte(直接用德文),他希望公司的品牌能像夏绿蒂一样受人欢迎。乐天旗下有很多品牌都冠名Charlotte ,包括剧院、电影院、酒店里的房间、巧克力等等。
读了这段文字,我唏嘘不已。这个故事,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商人爱文学可以爱到什么地步。另一方面,它是文学有用论和文学帝国主义的又一个有力的例证。辛格浩拿自己钟爱的文学形象来命名自己创立的公司,他的公司最后跻身世界五百强,这几乎令人疑心绿蒂这个名字具有祝福和保佑之效。拿文学形象为企业命名的,世界五百强里恐怕没有第二例(阿里巴巴也许是例外)。
既然如此,Lotte集团的中文名称为什么不是“绿蒂”而是“乐天”?如果是出于商业策略考虑,觉得“乐天”听着很吉祥、很喜庆、很容易讨中国的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情有可原。但如果该译法源于无知,如果是因为译者没有对这个明显不同寻常的公司名称做起码的词源考证,这种译法就应引以为戒。否则,假如需要从韩文转译托马斯·曼的Lotte in Weimar,《绿蒂在魏玛》就会变成《乐天在魏玛》。光看标题,中文读者很有可能把这当作一则关于辛格浩或者乐天集团的商业传奇故事。
把Lotte译为“乐天”而非“绿蒂”,这的确令一切文学爱好者感到遗憾,因为这种译法屏蔽了一个故事,屏蔽了一系列历史关联。但既然今天的乐天集团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译法表示欢迎,因为这样一来,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德国文学的爱好者就不至于陷入内心矛盾和分裂,就不必追问如此一个如此可爱的名字怎么给了一个如此讨厌的企业。
我要讲的第二个翻译之憾,是一个人名。也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在一次私人聚会上,我和一个新认识的德国人聊得很投机。他是做金融的,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会汉语,人也好玩。他用中文说他叫华德。一看就是致力于中德友好的意思,多好的名字。聊了一会儿,他递我一张名片,一看德文,我的眼睛亮了:Christoph Graf von Waldersee。克里斯多夫·封·瓦德西伯爵。谁是瓦德西?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姓瓦德西的不少,但是在姓氏前面加“封”(或者“冯”)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说,贵族世家瓦德西应该只有一个。我马上向他本人求证。没错。他是那位瓦德西的旁系后代。他对世纪之交那段历史倒是很感兴趣。他经常跑安徽,去黄山脚下看过赛金花的故居,还调侃说瓦德西在德国无后嗣,在中国未知。他还数次到合肥看博物馆,因为他对李鸿章感兴趣。我问他:您为什么取名华德?中文为什么不直接写瓦德西?您害怕遇到义和团的后代?他回答说:当然不是。当初他的中文老师直接按照德文姓氏即Waldersee的发音给他取名华德泽,他自己简化为华德。他承认,他的老师不太清楚那段历史,他本人当初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姓名已有固定的中文译法。由于取名华德,瓦德西伯爵几乎隐姓埋名地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是这种隐身效果并非故意而为,而隐身的瓦德西伯爵,于人于己可能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事实上,不仅是瓦德西,近代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名人都有固定的中文名字,而且那些名字都不是按照其西文名字的发音翻译而来的。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Matteo Ricci,大名鼎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是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大名鼎鼎的德国传教士兼汉学家、翻译家魏礼贤是Richard Wilhelm,等等。撞见这些外国名字的时候,如果无知而懒惰的译者简单粗暴地采用音译,必然贻笑大方。值得提醒的是,当代西方汉学家也延续了取中文名字的传统,因为他们普遍觉得自己的西文名字音译过来效果很不好,一般都会给自己取一个简洁、典雅、有文化内涵的中文名字。如果我们将其姓名简单音译,就将产生多种不良后果:第一,让其本人感到郁闷;第二,有可能屏蔽其汉学家身份,因为不少人知道其固定的中文名字;第三,还可能翻别的错误。对此,我举一个最近偶然发现的例子:柏林有一位在颇有名气的女性中国通。她的德文姓名是Bettina Gransow,中文名字是柯兰君。因为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我们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将其姓名直接音译为“贝蒂娜·葛兰索夫”,还非常诚实地用括弧标注了德文。然而,这是错误的音译。Gransow这个姓氏的最后一个字母w很诡异,有时候发音有时候不发音,二者区别很大。葛兰索夫,是斯拉夫人,葛兰索则是德国人或者说日耳曼人。据我所知,没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你把他(她)叫成斯拉夫人。
第三个例子来自书本,涉及历史人物的姓名。我们德语界常常有人把Moses音译为“莫塞斯”。这其实就是摩西。如此音译,其结果就是把路人皆知的犹太先知屏蔽了,或者是把相关的文学人物形象或者历史人物的犹太特征屏蔽了。普通译者犯这种错误大家可以一笑置之。但如果是知名学者,这后果就有点严重。我就看见一位大牌的德国史专家在文中提到自己曾做客莫塞斯·孟德尔松研究中心。实际上,那是摩西·门德尔松研究中心,德文是:Moses Mendelssohn Zentrum。就是说,姓和名都译错了。这种译法将作者的专业知识硬伤暴露无遗。摩西·门德尔松是和康德比肩而立的哲学家,是第一个在德国文化界获得巨大声誉的德国犹太人。你赫然写下莫塞斯·孟德尔松,你的同行和业内人士马上就知道你为什么犯这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没读过德文版《圣经》,或者你没研究过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或者你不关注德国的启蒙时代和启蒙哲学,或者你从未读过相关德文文献……总之,这个“莫塞斯·孟德尔松”可能成为学界英雄的阿克琉斯之踵。需要补充的是,不识摩西真面目的并不局限于德语界。我还见过一个法语界的知名学者的书中见过“莫歇”——这无疑是“莫塞斯”法语对偶。
人名、地名错译可谓比比皆是,而且屡屡出现在知名的学者和译者笔下。德语界常见的有:把Karl der Große译为卡尔大帝,这其实是查理大帝;把Sankt Franziskus译为圣弗朗西斯库斯,这其实是圣方济各;把von Moltke译为冯·莫尔特克,这其实是普鲁士元帅、普法战争的头号功臣毛奇;把Perikles译为佩利克勒斯,这其实是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把Ludwig XIV译为路德维希十四,这其实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然,对于德语界这类低级错误,法语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报复。在一本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书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Louis II de Bavière)就变成了“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
跨语种翻译人名、地名的确容易犯错误。我在翻译瓦尔泽小说《童贞女之子》的时候,曾把人名Modest 音译为“莫德斯特”,交稿之前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瑞士-俄罗斯混血儿,才赶紧按照俄语发音改成“莫杰斯特”。
我在英语界看见的两个翻译奇葩同样富有启发意义。
一朵奇葩来自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德国旅游手册里面。在介绍吕贝克的一章,托马斯·曼其人其作自然要出现。但是我看见一部陌生的作品:《福斯图斯医生》!我的天。这不就是Doktor Faustus、不就是《浮士德博士》吗?我感到诧异的是,那位译者下笔的时候似乎完全处于问心无愧的状态:Doktor不是医生又是什么?Faustus不念“福斯图斯”念什么?
另一朵奇葩来自地名翻译。一位译界大腕儿在他的大部头里面讲述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翻译成英文会面临多少选择、多少烦恼。这个剧本叫《塞丘安的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对不起,这可是路人皆知的《四川好人》!这一错误让我耿耿于怀,不仅因为我是四川人。更让我想不通的是,一个翻译理论大腕儿怎么会犯这一现象级的错误。好吧,你不是搞德语文学的,你也不怎么搞文学,而且Sezuan也不是Sichuan,不是现在汉语拼音。可是,你知道塞丘安在哪里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查一查有关布莱希特的百科词条?你可不可以翻一翻《世界地名辞典》?如果这里找不到“塞丘安”,你可不可以查一查《月球地名辞典》。如果月球上也找不到“塞丘安”,你是否应该来点自我怀疑?总之,这个《塞丘安的好人》也属于出口转内销的翻译奇葩,可以跟“孟修斯”(孟子)、“蒋凯申”(蒋介石)、“孙雅森博士”(孙逸仙医生)媲美。
类似上述的翻译奇葩,译界还有千千万万。产生这类错误的原因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无知加懒惰。这些译者首先是缺乏匠心,不懂行规,没有做到勤奋、认真。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工匠精神,要呼吁翻译同行至少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要牢记“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这句鲁迅名言,在翻译中遇到每一个陌生的人名、地名、术语都应如临大敌。不经查验和查阅,不能随便翻译人名、地名和概念术语。为此,除了各类普通外汉词典,我们要频繁地查阅权威的世界地名词典、权威的姓名译名词典、权威的专业词典,包括各类相关在线辞典。
其二,要把每一个人名、地名和术语概念的翻译都当作一门学问。涉及术语和概念的时候,要有“隔行如隔山”的意识,对于普通外汉词典的释义要保持高度警惕(若从这一角度理解,“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这句格言是否还有一层涵义?),随时请教活辞典,即各路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
当然,这些规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想吧,翻译一部小说或者学术著作,我们将遇上多少人名、地名和术语?而如果我们严格按照上述规则或者流程来处理每一个人名、地名和术语的翻译,那是多大的工作量?得惊动多少内行和专家?为了说明个中滋味,我就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先说人名和地名。前一阵我对《雷曼先生》的译文进行再版修订,街名翻译更是做了大面积修改。十五年前,我完全按照德语发音和约定俗成的惯例翻译街名。最近几年才发现,德国人的地方志做得非常地好,堪称完美。他们记录了每一个街名的来龙去脉,而且供人随便进行网络查阅。《雷曼先生》全部采用柏林的真实街名,几乎每一条街都有一个典故,大都涉及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对比这些典故之后,发现过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为没有体现出典故。譬如,我把“库弗利大街”改为“居弗利大街”,因为这个街名旨在纪念于本地的一个政治家,但他是法裔德国人,所以必须按照法语译名规则。再如,我把“奥拉宁大街”改为“奥兰治大街”,因为这条街是根据荷兰王室命名的,众所周知,荷兰王室始于奥兰治亲王。再如,我把“斯卡利泽大街”改为“斯卡利采大街”,因为它得名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斯卡利采战役,斯卡利采在今天的捷克境内。如此翻译,知识增长不少,工作量也翻出好几倍。
十几年前,我在翻译《批评家之死》的时候碰上一个生词。根据上下文,我知道这是盛酒的器皿,德汉词典将它译为“大腹车料瓶”。我感觉这是鬼话。但是人话去哪里找?既然是人话,那就找人打听。可是,在红酒消费尚未变成中产时尚的年代,没几个人知道这叫什么。最后我把电话打到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西餐厅,找到领班,找到了标准答案:醒酒器!如今,设计优雅、造型独特的水晶醒酒器已经成为贵族化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喝酒标配,成为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批评家之死》提到这醒酒器,也是为了彰显女主人的生活之优裕。
翻译《童贞女之子》之后,我更是频频求助于各路活词典。我向神学家请教过,因为小说中有大量圣人圣名,还有不少涉及教堂器皿和教会礼仪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普通词典里查不到,或者词典释义不太靠谱;我向摩托车赛车手请教过,因为小说中出现一些涉及摩托车比赛和摩托车改装的专业词汇;我还请教过音乐指挥,因为小说中多次描写合唱排练场面,个别专业的表达没有指挥的钦定我根本就拿不出手,等等。
译界的第三条行规,是约定俗成。所谓约定俗成,就是遵守先后秩序,接受早已固定并且被广泛接受的翻译。要承认,这一行规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旨在保证人们交流和沟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不问是非、不讲逻辑、不关心真善美。有关实例不胜枚举。
查理大帝算法兰西人还是德意志人,这个问题没有定论,也不可能有定论。若是德意志人,中文当然应该叫卡尔大帝,但“查理大帝”在先,写“卡尔大帝”就属于错误,就说明译者不读过相关中文文献。
海德堡应该叫海德堡吗?不应该。我们德语界的宗师级人物冯至先生早就否定了这种译法。冯先生早年留学海德堡,在海德堡拿了博士学位。他对内卡河畔这个美丽的小镇了如指掌并且充满感情。冯先生是学者。作为学者,他认为“海德堡”完全名不副实:如果音译,应该是海德贝格,若是音义结合,应该译为海德山。冯先生又是诗人。作为诗人,他想出一个音义兼顾而且充满诗意的译名:“海黛山”。可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海黛山”终究未能推广开来。原因很简单:冯先生是后来者。这是冯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慕尼黑这个地名译得好吗?当然不好。一是不符合德语发音,二来笔画太多,再者,结尾还是个黑字!谁不知道人家巴伐利亚首府一向以阳光明媚、色彩绚丽著称?因此,我们德语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直呼吁用德语音译即“明兴”代替“慕尼黑”。但呼吁未果。
前面说到“乐天”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译名,是因为它屏蔽了歌德的小说,屏蔽了企业创始人对歌德小说人物的景仰。但鲜为人知的是,歌德小说的中文标题——《少年维特之烦恼》——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翻译。一来维特不是少年,而是青年,德语写得一清二楚,;二来维特不是死于烦恼,他的脸皮没那么薄,而是死于苦难或者痛苦。这个德文也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这最最有名的德文小说本来应该译为《青年维特的痛苦》或者《青年维特的苦难》。而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神学的阐释,相信维特之死是对基督受难的戏仿,我们又可以将它译为《青年维特受难记》。然而,任你道理说一千说一万,众人还是只认《少年维特之烦恼》。本人也觉得《少年维特之烦恼》念着挺顺口。这叫习惯成自然。
美国的参议院和罗马时代的元老院不是一个词即Senat吗?是的。就是说,中文本来可以译为“元老院”,因为当初美国人的确有向元老院看齐的意思。“参议院”这一译法屏蔽了美利坚合众国和罗马帝国的思想渊源。如果我们今天说的是“美国国会元老院”而非“美国国会参议院”,我们的政治思考是否会受到一点微妙的影响呢?
我看到的最最令人遗憾的翻译,是犹太人的犹字。本来,我们中国人属于世界上最能咬文嚼字的民族,我们对文字的推敲堪称世界冠军,甚至搞出过文字狱。我们也许是唯一把文字视为总体艺术作品的民族。我们既看重其义,也看重其音,同时看重其形。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坚持对外友好的民族,喜欢给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取好听又好看的名字,如英国,如美国,如法国,如德国。可是,我们唯独给古老而智慧的犹太民族来了个不太雅观的反犬旁。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得不说,我们亏大了。西方有上千年的仇犹、反犹、灭犹的历史,我们则是一个善待犹太人的民族。开封的犹太人跟我们和谐相处,最后还融为一体水;二战期间我们在上海对惊魂未定、四处漂泊的欧洲犹太人张臂欢迎。众所周知,这段历史决定了以色列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可是,这个反犬旁哪里来?无人知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习惯势力太可怕,犹太人三个字改不了。我们只能喟然叹息。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自然过渡到三位一体和文学翻译的话题。为什么说匠心、学问、灵感构成三位一体?原因很简单:翻译需要匠心,有了匠心,翻译才能体现学问,有了学问,才能得到灵感。严复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说的就是必须通过长时间的推敲和研究才能得到灵感。三位一体论适用于所有翻译,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对此,我照样用实例说明。
例一,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这部小说是傅惟慈先生翻译的,译得非常好。但是里面有一个词,不仅傅老先生对付不了,而且谁也对付不了。这个词就是Bürger。翻开德汉词典,都会看到如下释义:市民,小市民,公民,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翻译的时候则常常令人茫然不知所措。譬如,当小说中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他比你更不像Bürger”的时候,我们选哪条释义合适?傅老先生选择了“市民”。可是,什么叫“他比你更不像市民”?市民长什么样?显然,这译法有点问题,但是我也想不出更好的翻译。这是2004年的事情。2007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还特地召开一个跨学科的中德学术讨论会,让来自哲学、法学、文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围绕这一概念展开讨论。认识收获了一大堆,翻译却毫无进展。后来,在研究波希米亚人(这个概念也属于翻译之憾!)的过程中,我才恍然大悟:作为波希米亚人的对立面,市民或者资产阶级不就是庸俗的同义词吗?庸俗不就是“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的一个历史内涵吗?答案有了:“他比你还脱俗!”
例二,瓦尔泽小说《第十三章》。
小说中讲到一个男人天天等一个女人的邮件却总是等不来。一天,他在电脑页面上又看见那句令人沮丧的提示语:“未找到搜索项”。于是他来了一句“这是翻译”。这话我一时没看明白,而且如果就这么译过来,读者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经过研究才明白,“译文”是一则瓦氏概念内涵,跟瓦尔泽对翻译的认识有关:他对翻译很不放心,深知翻译和原文之间存在多大距离,所以,这个地方的“翻译”就是“蹩脚的文字”。换言之,因为等不到邮件,小说的主人公已由沮丧变为愤怒,而且把怒火发泄到电脑上面,可以说是对那句电脑提示进行了人身攻击。明白这层道理后,我脑袋里才灵光一现,给他加了一个字,译为:“这是翻译腔”。换言之,在这种时候,翻译的突破口只可能是概念的内涵(德语:Konnotation,英语:connotation)而非外延(德语:Denotation,英语:denotation)。
例三,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
小说第六章的结尾主要写好兵约阿希姆·齐姆森的死亡和善后事宜。文中有两个绝妙的文字游戏,现有的两个译本可惜都没有翻译出来。发现问题之后,我跟着苦苦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文字游戏出现在对一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衣着的描写。在一个译本里可以读到:“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一件庄重的短外套,粗粗的手上戴一只结婚戒指,手指肥胖,使黄色的箍都已经陷进肉里,被埋住了,别人还觉得他的外套散发出一股尸臭味,实际上,这是偏见。”这段文字译得很好,只是“庄重的短外套”不够完美(另外一个译本说是“短褂”,意思就差远了)。这一译法符合词典释义,但未能体现反讽家托马斯·曼的良苦用心或者说险恶用心。因为这里所说的短外套德文是Bratenrock,硬译过来是“烤肉外套”,源于德国中产阶级身着礼服赴烤肉晚宴的习俗。今天很少有德国人去关注这个词的来源或者字面意义(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注意犹字所带的反犬旁),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一典故。但是,托马斯·曼偏偏要激活早已被人遗忘的字面意思,并由此勾勒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穿着“烤肉晚宴礼服”出现在众人眼前,人们觉得这“烤肉晚宴礼服”散发出一股尸臭……接下来的描写又表明,此人最清楚什么是死者的尊严,是所谓的虔诚王国的合格卫士。很明显,缺了“烤肉晚宴礼服”,这段文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打点折扣。
《魔山》第六章的另一个文字游戏,是施托尔夫人的口误:她连哭带喊要求在约阿希姆下葬时奏乐。她本想说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德文是Eroica,结果说成了 Erotika,一字之差,耐人寻味。鉴于弗洛伊德思想踪迹在小说里面时隐时现,施托尔夫人说话也经常有意无意地素面荤底,我们可以断定她的口误并非偶然,暴露了不太洁净的下意识。因此,我们就应寻找一个既能保证一字之差、又能体现色情意味的作品名称。谢天谢地,《英雄交响曲》里面有“雄”和“交”!《雌雄交响曲》如何?
今天我举这么多的例子,其实就想说明如下两点:
第一,文学翻译距离非文学翻译并非一般所想象地那么遥远。不言而喻,文学翻译的对象自然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则具有形象性、音乐性、自反性(反观作品和语言本身)、游戏性(游戏文字、重内涵而非外延)等显著特征,从而有别于日常语言、学术语言、公文语言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相距甚远。可是,如果着眼于当今世界的主导文学体裁长篇小说,我们又可以说文学语言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文学性或者说杂语性。我们知道,一部宏大的长篇小说就是一大盘话语沙拉,就是一盘话语大杂烩。里面既有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又有来自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的名称,还有俚语脏话大白话口水话,等等。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恰恰是由长篇小说的崇高使命或者说哲学使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现代长篇小说肩负着勾勒完整世界图景的重任,它描写自然,描写社会,描写人生,描写人性,它必然有长度、有广度、有深度,还有相当的复杂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有多么丰富多彩,长篇小说的语言就有多么地丰富多彩。
第二,文学意义常常是通过非文学语言的专业运用生成的。就是说,非文学的词汇翻译得越地道、越准确、越专业,其文学意义就越明显,获得翻译灵感的几率就越大。因此,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匠心、学问、灵感也必然是三位一体。
我希望自己把道理说清楚了。
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文津阅读,2017年6月29日
https://mp.weixin.qq.com/s/m8edcCmZLl-WxEZR75oj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