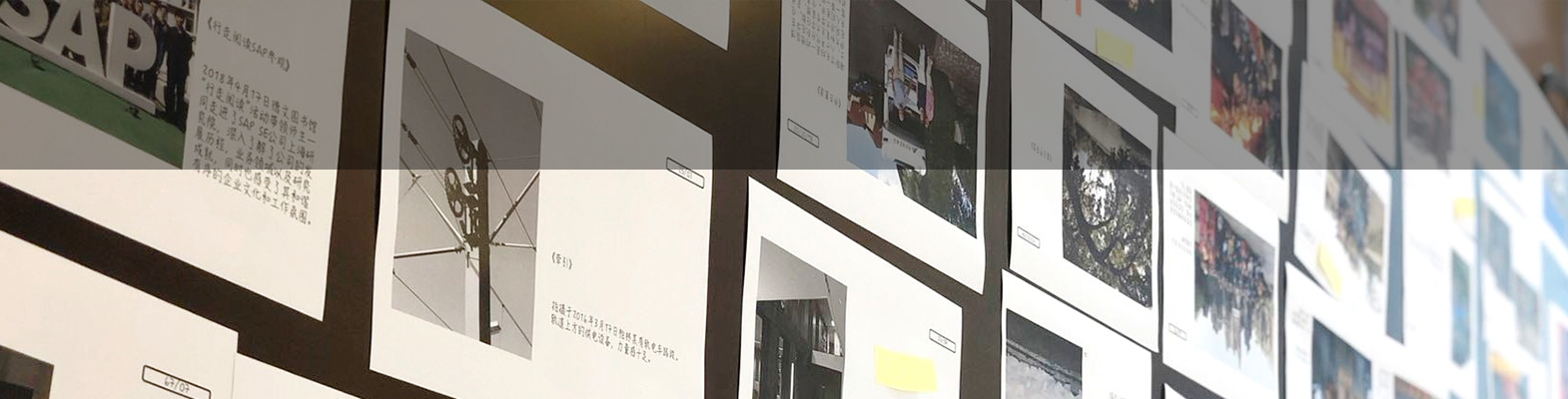作者介绍
张维: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获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博士学位,同年在国际首次求得环壳在旋转对称载荷下的应力状态的渐近解。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创办深圳大学并任首任校长,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逝世。高晓松外公。
本文是张维同志1999年所作。

张维教授 © WEGZUDE留德圈

张维教授与家人合影 © baike.so.com
(一)向往
为什么要去德国留学?回想起来,似乎不是偶然的。
我的二叔父张仲苏(早年名张谨)1905年被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选派,与顾孟余、李仪祉同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1913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京师学务局(相当于今日的市教育局)局长,同济大学校长,河北大学校长。由于父亲英年早逝,二叔对我们兄弟较为关怀,时常对我们讲述在德求学的情景,并对德国工业产品的质量交口称赞。这使幼小的我对德国有了良好的印象。
1919—1929年,正值我上高小和中学。那时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日益加剧,更兼官员腐败,经济衰落,民不聊生,亡国灭顶之灾似乎就在眼前。救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愿望。这一时期在我心中逐渐形成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心刻苦读书,不但要上大学,而且希望有朝一日到国外去进一步深造,求得更高深的学问回来报效祖国。到哪儿去呢?因受叔叔的影响,隐隐约约地把德国当做了第一目标。
后来,我与父亲的世交陆家的姑娘陆士嘉逐渐有了感情。她那时在北师大念物理。因对德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十分景仰,很早就产生了去德国深造的愿望。我俩订婚之后,更是志同道合,常常相互鼓励,一定要实现留学德国的梦想。
因为父亲去世较早,全家五六口人只靠一点遗产和哥哥大学毕业后的工资维持生计,家庭经济状况属中等偏下,自费留学绝无可能。可公费留学又没有德国的名额,因此能否一起赴德求学便成了我们经常讨论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1937年,我有幸考取了中英庚款的留英公费生。与未婚妻士嘉同船出国。可惜一人留英,一人赴德。念到寒假,我便由伦敦去了德国,一方面看望半年没见的未婚妻,另一方面考察德国在土木工程和力学方面的教学情况,了解到柏林高工(今日的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水平很高,并设有薄壳理论等世界最先进的课程。这更加强了我要到德国深造的愿望。
回到伦敦后,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得到中英庚款管委会的批准,于1938年暑假转学德国,从小留学德国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能与士嘉同在一国求学更使我高兴,虽然她去了葛廷根,我则留在柏林。
(二)德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
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我从德国学到了不少东西。
研究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追求(相对)真理和掌握规律。德意志这个民族性格非常严肃认真,做什么事都要求彻底和准确,这也体现在学术上。他们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事一件工作,研究一个问题都非常彻底。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还表现在德国学者善长撰写的大部头百科全书上。本世纪前半叶德国出版了很多各类成套的百科全书和手册。其数量之大,体材之广,论述之精辟,在其他国家是少见的。
柏林大学校长,普鲁士王国教育部长,著名的威廉·洪堡的高等教育思想——大学必须是研究与教学并重——影响十分深远,成为长时期德国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并对全世界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我所受益的德国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我直接有关的老师接触获得的。
第一位学者是我的德语老师。
很早以前,为了准备赴德留学,我就想方设法学习德语。我认为到一个国家去念书,必须先学会那个国家的语言。因为语言是掌握知识,交流思想,了解异国文化和生活的工具。但是在30年代的北平买本德语文法书都很难,更不要说找个正宗的德国人做老师了。有一年暑假,好不容易从北大物理系夏元溧教授的德国夫人那里学了一点启蒙的文法。后来在唐山交大做助教时又跟一位在开滦煤矿工作的德国人Wolff先生每两周一次学了点儿。直至到了伦敦又找到一位德国侨民继续学德文。但这些零七八碎的努力全然没有使我的德语水平超出启蒙阶段,即只知der,die,das的各格变化。等到了德国正式学习德语时,不消一周,已然超出在国内和伦敦努力的总合。
1938年夏我到柏林以后,根据陆士嘉的经验,我没有参加柏林大学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的德语班,而是请私人教师单独授课。我的教师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退休教授赵林克悌。她的德文名字是Starloff Linke。本来她在葛廷根大学学历史,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疯狂迫害犹太人。Linke小姐可能有1/8犹太血统,因此被免职,只好为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教德文。
Linke小姐的教学法灵活多样而又要求严格。她每天早上来我住处一小时,先是改前一天的作业,教文法,随后学新课文,再是十几分钟的会话,临下课前留下家庭作业。这些作业足够我一整天去“抠”。就这样我在她严格要求下紧张地学了三个月的基本文法,积累了一些词汇,学校一开学,我便顺利地注册上课了,但德语课仍然每周两次。如此坚持了一年,打下了较扎实的语言基础。
我的专业导师Friedrich Toelke教授是我在德期间接触最多,受益极大的德国学者。他任教的全校工科各系的基础课工程力学课分三个学期授课。在教学方法上,他授课内容系统清楚,讲课生动,语言精炼,字句清晰,既无废话,也不重复,且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如果将他的讲课录下音来,可以说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他还时不时地讲个笑话,使我们紧张的情绪放松一下,效果很好。因此大家在他的课上时常跺地板(德国学生习惯不用鼓掌,而用此法表达赞赏)。
在研究工作方面,他善于从工程实际中提炼出力学的理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展了理论。他的研究范围涉及诸多工程方面,如结构工程,水利工程,船舶结构,输油管道的振荡及石油勘探中的地震波。从他指导下的研究工作中,使我的眼界大大超出了原来在国内的单一的土木工程中的结构力学的范畴,研究的思路开了窍。
Toelke教授对研究生的指导方针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每隔三四周见一次面,听他们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和想法,然后加以指点。研究生自己找参考书,想研究方法,听补充课程,他从不过问。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具有独立的、创造性的解决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我的第二位导师Franz Dischinger教授对研究生的要求更高,连博士论文的题目都要自己去选。他常说:“我这里不开博士工厂。不管出论文题目。”从而拒收想跟他要论文题目做博士生的人。谁有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可以呈送给他,请求答辩。
关于我在柏林高工土木工程系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事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按照德国学位法的规定,必须是获得德国高等工业学校文凭工程师(Dipl.-Ing.)学位的人,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才能申请攻读博士。我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工学士,又工作了四年,后又获得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文凭(Diploma of Imperial College,即DIC),这在国际上相当于硕士学位,在德国相当于文凭工程师学位。不料导师把我的材料报到学校后,校长就是不批准。从1939年一直拖到1941年。最后报到了当时的德国教育部,得到部长批准,我才正式获得博士生资格。其实在此之前教授已开始指导我的论文工作了。由于1942年2月我开始担任助教工作,需要用较多的时间帮助教授工作,加上后来空袭日益增多,工作效率颇受影响,因此我的论文答辩一直拖到1944年10月才完成。
德国治学精神方面给我更多影响的是葛廷根大学的Ludwig Prandtl教授和Robert Pohl教授。Prandtl教授是陆士嘉的导师,我和他直接接触只有几次,没有更多的机会亲聆他的教诲,然而他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August Foeppl(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之为葛廷根思想(Goettinger Geist)。什么是葛廷根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发展了力学的基本理论,反过来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它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
Pohl教授在试验物理方面世界驰名。他的“大学物理”出版到十五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许多插图都是Pohl教授亲自做的实验照片。他常在课堂上实际表演各种物理现象,学习气氛生动活泼,并使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观察自然现象,为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二战期间在德生活
自1938年7月到德国至1945年9月离境去瑞士,我经历了整个二战。这段生活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八年的留学生活变化很大。战前的一年和战争初期,日常生活尚属正常。在住的方面,当时德国大学极少有学生宿舍,外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进去。在柏林我们全是租房子住。房东多半是退休职工,月租金在30~40马克。而一般官费生的生活费每月110~140马克(个别国民党高官子弟情况不详)。在食的方面呢,学校设有学生食堂(Mensa),午餐份饭70芬尼。而晚饭则往往到中国小饭馆吃。一来德国政府为照顾中国侨民,配给几个中国小饭馆大米,二来在那儿能碰到同学,聊聊天,交换些大家关心的国内抗战的消息。但因此说德文的机会就比在其他城市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初抵柏林时,我的德语才是初级阶段。对于哥德体的花草字很不习惯,因而闹过笑话。那时为了省钱,我和士嘉往往去图书馆看书,中午啃面包,晚上自己做或吃中国小饭馆。有一回我们想开开洋荤,便到一家德国小饭馆去吃午饭。饭馆的菜单是手写的花体字。我的德语虽然初学,但很想练练说话。也没跟士嘉商量,就捧着菜单对女招待说我要“Kinderfleisch”。女招待笑眯眯地说:“我们这里不卖Kinderfleisch。”我再一看菜单,原来上面写的是Rinderfleisch。我因不识花体字,分不清R和K,竟然把花体的R看成K。这样,将“小牛肉”就说成了“小孩肉”。这一道吓人的菜令四座的顾客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好不尴尬。
这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占领了捷克,实际上进入了半战争状态。重要的食品已分别开始实行配给制,凭票供应。黄油每人每月500克,这对于中国留学生还过得去。到后来食品供应一年紧似一年,黄油渐渐减到了每周250克,125克,乃至50克。肉的供应到了1943—1944年已减至每人每周50克(一两),连塞牙缝都不够。德国家庭还多少有点农村亲戚,而我们外国人就苦了。于是我们只好想方设法找点油水。1940年,我和士嘉听说临国卢森堡农村供应较好,就去那里度暑假,其主要目的是想买点肉食。费了半天劲,勉强买了一条火腿。后来这条路子断了,我们又利用存在瑞士的钱邮购可从境外寄到德国的“Liebespaket”。那里边有黄油、熏肉、咖啡和糖。咖啡对我们不重要,就送给房东。
到了战争末期,因为柏林轰炸得厉害,我便辞去助教的工作搬到葛廷根。这时我们已经结婚,并有了女儿克群。从1945年初到5月德国投降,这几个月的日子最为困难。每人每周只能买到一个两公斤的褐色枕头面包,里面掺有大量的土豆粉。买来之后还必须放个两三天,等到硬了之后再切,才能不粘刀子。一个面包分成七份,每天一份。加上又没什么油水,每天晚上10点,我的胃就咕噜咕噜地响,比闹钟都准。幸亏士嘉通过Pohl夫人认识一家由几个老姑娘开的面包房。那几个人对中国人挺友好,常常暗中不剪面包票,多卖给我们一个。这点东西可解决大问题了。就这样我们熬到了德国投降。盟军过来的第一天给盟国的难民每人发了一个红烧牛肉罐头,我一口气便把那个罐头吃了个精光。这时候我一米七的个儿体重只有56公斤。
在柏林的那几年除了上课和搞研究外,在生活上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在中国同学中打圈子。有两个活动值得一提。一个是德文夜。另一个是健会。
为了弥补在柏林说德文机会少的缺点,有几个先来的同学在Linke小姐的倡议下组织了一个“德文夜”(Deutschabend)。每星期六晚7点到10点在谢家泽和周源祯同学住处聚会。参加者有十来个中国同学和几位德国男女学生,当然还有Linke小姐。每次有一个主题,大家各抒己见但只许说德文。我因为跟Linke小姐学过德文,经她介绍便也参加了,并觉得受益匪浅。这个活动坚持了两年多,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局势趋于紧张,就停止了。
健会是由一些爱好运动的同学自觉自愿组成的,有十几位热心的参加者,大多是柏林高工的学生,还有几个柏林大学的,我是其中之一。大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练好身体报效祖国。柏林西郊有个奥林匹克体育场,还附带有室内游泳馆。健会会员们每星期六下午乘高架车(S-Bahn)到那里游泳或做其他体育活动。记得那时常常组织各种比赛,文笔好的同学还把每次的赛事记录在案。我虽然积极参加,无冬立夏每周必去练习游泳,但是到底也没学会换气。每次测验都是勉强游到25米处就完事了。至今仍然后悔当初没认认真真把游泳学会。不过在网球比赛上还是小有成绩的。这几年的锻炼对身体健康确实大有好处。
就这样,我们虽然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德国,但在德国政府仍想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基本上还可以照常学习和研究。到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发动战争,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后,我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大使馆撤走,德国政府承认了汪精卫伪政权。这样一来。我们的中国护照到期延长之事就只能寄到我国驻瑞士使馆去办。在德国我们成了无国籍的侨民了。幸而德国政府还不想为难这些人,警察局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战争期间最大的烦恼是跑空袭警报。战争初期英美还没有制造出四个发动机的远程轰炸机。从英国起飞的飞机也还到不了柏林,我们在柏林还能天天睡个好觉。到了1941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变化。英美的轰炸机有时也光顾柏林,甚至到过德累斯顿。1942年2月的一次大轰炸造成了德累斯顿20万居民的死伤。大家顿感紧张起来。各个居民楼纷纷将存储土豆用的地下室加以改建,以做防空之用。
1943年11月,大规模的轰炸开始了。这类轰炸每次半夜12点左右进行,英美往往是出动2000架四个发动机的Lancaster轰炸机。先是四架定位飞机投放照明弹,随后那两千架轰炸机就向四边形之内的地区投炸弹。俗称地毯式轰炸。对于盟军的轰炸,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希望他们狠狠地炸纳粹,又盼望炸弹长上眼睛,别往我们头上掉,我还盼着能安全地回家呢。
同在柏林高工学力学的刘先志夫妇所住的楼房在一次空袭中被命中,上层塌下来将防空洞的几个出口全部堵死。这还不说,因为地下室水管破裂,自来水大量涌出。电也断了,人们站在漆黑一团的地下室里,一边被满屋子的灰尘呛得喘不过气,一边感到水在不断地上涨,先是没过脚面,然后涨到小腿,眼看面临着灭顶之灾,地下室内一片哭叫。幸好有一个防空员摸到了通往另一栋楼房地下窖的临时隔断,众人将它推倒,人们才算捡了一条命。刘先志夫妇吃了这回惊吓,再也不敢呆在柏林了,不久便转学去了葛廷根大学。尽管那里从未挨过轰炸,可他们俩已成了惊弓之鸟。每晚一响防空警报,俩人就提着放论文的小箱子跑到附近小山坡上宁可冻着直到警报解除,也不在家里。防空洞是说什么也不肯钻了。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一回。1943年11月的一天夜里,柏林受到第一次大轰炸,而且是两千架飞机的大规模轰炸。刹时间全市的水、电、煤气全都断了,整个城市一片恐慌。次日,中国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康德大街的老于饭馆。大家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三天里还会有大轰炸,于是建议我和士嘉去西郊的好友孙德和家暂住。我和士嘉赶紧回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两个箱子。这时已是下午5点,黄昏的街道人烟稀少。我们提心吊胆地上了高架车,才走了两站,到了西十字路口站,空袭警报刺耳地响了起来。车停了,我们提着箱子,跌跌撞撞随着人流钻进了一个临时的防空洞。不一会儿,只听见“咣!咣!”的几下爆炸声,震耳欲聋,防空洞摇摇欲坠。解除警报后,我们爬出来继续上车。第二天在老孙家见报,说日前西十字路口站防空洞被直接命中,死伤甚多。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西十字路口站两头各有一个防空洞,我们钻的那一个侥幸没被炸着,真可算是命大呀。
二战到1945年5月宣告结束。此时的德国包括欧洲各国在内均遭到空前的破坏。德国的工业几乎没有了,煤矿完全停产,过冬的采暖成了大问题。葛廷根的盟国占领军司令部发给每家一张券,凭此可以自己去附近的山上伐一棵树,当作冬季取暖的木柴。有生以来头一回上山伐木,还挺新鲜的。我和士嘉拿着斧子,跟房东Pohl教授一家一同上了山,只见凡是达到可伐年龄的树都已做了记号。于是花了半天功夫各自伐了一棵拉回家来。到了9月我得到瑞士一家机械厂的聘书,并获得批准可以出境,便把这棵树送给了Pohl教授。他们一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比别人家多一倍的柴火,冬天可以暖和一些了。
(四)纳粹的独裁统治
1933年1月希特勒获得了政权,立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西斯统治和镇压。他对于德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实行的排挤和迫害真是史无前例,惨无人道的。凡是稍有不赞成纳粹的,或三代之中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一律开除公职。我的德语老师Linke小姐就是一例。
德国传统上每年出版一本全国学术界的名人录,叫Minerva。1933年的Minerva一下子比1932年的少了1/3。就是因为希特勒一上台,首先就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里对不赞成法西斯的人士开刀,将他们抓的抓,赶的赶。也有些人看不过纳粹的独裁统治,主动离开他们的祖国,到外国流亡。我所在的教研室前任主任Hans Reissner教授就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免职,被迫去了美国。他与钱学森同志的老师Theodore von Karman教授当年在德国是齐名的。von Karman教授有先见之明,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离开了德国,而H . Reissner教授则是在1933年被解职以后不得不离德去美。可惜他在美国不被重用,在一个不出名的大学里默默无闻地去世了。
希特勒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12年(1933—1945),最残酷的罪行莫过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了。希特勒上台伊始,先是排挤犹太人。大中学里犹太血统的教师、教授纷纷被迫出走,大多数去了美国。这对德国学术界是个极大的损失。自由职业中犹太血统的医生和律师也被禁止开业。有办法的人逃离了德国,没办法的或留恋德国的便失了业在家闲住。后来均被弄到集中营杀害了。开始时部分小贩还被允许开业,战争后期也全被杀害了。
由于犹太人出生时均在犹太教堂受洗礼并登记在册。纳粹政府按册搜索他们,非常容易。自1941年以后所有还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胸前必须佩带黄色五角星以明确身份。公共汽车上不许犹太人坐,食品配额也少于一般居民。1943年以后,犹太人开始大批地被送往集中营,后来听说全被瓦斯熏死。我在柏林先后住过的几家犹太房东竟无一幸免。连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的犹太人也在劫难逃。
纳粹对于中国采取了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因为中国在战争初起就站在英美一边,因而对我国采取不友好态度。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幻想蒋介石与日本讲和,好让日本腾出手来向苏联的远东进攻。所以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很长时间仍呆在重庆不撤。直到苏德战争打起来,因我国向德国宣战,他才不得不撤回国。
但是纳粹党徒们对待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是歧视甚至是敌视的。士嘉就曾受过这种敌视。1943年因柏林常受轰炸,她就辞去了工作回到葛廷根。经她导师Prandtl介绍,到了著名的空气动力学试验所(Aerodynamische Versuchsanstalt,简称AVA)。该所当时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试验中心。那时的所长是Betz教授,但实际管事的是秘书长Dr.Riegels。那家伙是个顽固的纳粹党员。在士嘉拿着P教授的介绍信前去商谈工作问题时,他反复询问士嘉对日本侵华的看法。士嘉自然是表示义愤,因此被拒之门外。
我的导师也是一个纳粹党员,他经常在听完我的工作报告后问我中日战争如何了?蒋介石为何还不与日本讲和?我就给他讲一番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等等。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他总是说:“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两人握手再见。过了几周我再次汇报工作时,后半段时间又如此这般地重演一遍。不过倒也还能“和平共处”。
中国同学在战争年代在德国一般来说在政治问题上不主动表态,因此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但也有例外。据我所知,有一位叫翁真的同学,他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柏林高工学电机工程,平时不问政治。一日忽然失踪,据与他接近的同学说是被秘密警察(Gestapo)抓走了。原因是他有一德国女友,那女孩因为什么事被捕,Gestapo在她的笔记本上看到翁真的名字和地址,就将他也抓去了。当时大家曾努力想营救他,但我国驻德使馆业已撤离,无法可想。以后再也没人听到过翁真的消息。估计他已在集中营里遇难了。对于纳粹分子不友好的挑衅行为,我们则均予以反击。让那些家伙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五)别了,德国
1945年1月,我搬到葛廷根,与妻子女儿团聚。那时我们已看到纳粹的末日即将到来,于是就整日去数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阅读文献,一方面是等待解放,同时也想多带点知识回国去。
5月2日,美军占领了离葛廷根仅50公里的卡塞尔。又过了一周终于进军葛廷根。那天早晨我们听到隆隆的炮声,心里高兴极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与Pohl一家到地下室去躲避。不一会儿,由低矮的窗口看到端着冲锋枪的美军士兵紧张的身影。Pohl教授吐了一口气说:“这下好了,我们解放了!”大家立刻欢呼起来。二战对我们来说终于结束了!我的声音尤其大,因为想到可以回国了。Pohl教授招呼我:“张先生,咱们到地下室酒窖,挑一瓶好酒来庆祝胜利吧!”我喝着在德国生活八年以来第一次尝到的有名的Mosel葡萄酒,百感交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
结束语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心思立刻转到回国的问题上来了。这时欧洲与亚洲的交通无论是经由苏联的陆路还是走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的水路均不通。战争虽已结束,回归祖国之事却仍是遥遥无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期刊上获知瑞士苏黎士的Escher-Wyss机械厂承担了我国东北小丰满水电站的水轮机的制造。想到学了水轮机的设计技术,回国后可以为国家的水电建设服务,就请导师Toelke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等了几个月一直没有回音。7月的一天在路上巧遇瑞士驻柏林领事,得知他与该厂总经理相识,于是请他代询究竟。不久收到该厂来函,聘我任工厂研究工程师。有了在瑞士工作的证件,盟军司令部才批准我们离境,瑞士政府也才同意签发入境证。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和季羡林、刘先志夫妇共六个人由盟军派了一辆中型吉普,由一位美军少校护送,一位法军上士开车,将我们送到德法瑞边境的巴塞尔城,从此结束了我留德八年的充满了酸、甜、苦、辣的生活。
1999.3
资料来源:清华校友总会网站,百年清华,校友故事,2009年6月15日
http://www.tsinghua.org.cn/xxfb/xxfbAction.do?ms=ViewFbxxDetail_detail0&xxid=10026050&lmid=4000382&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