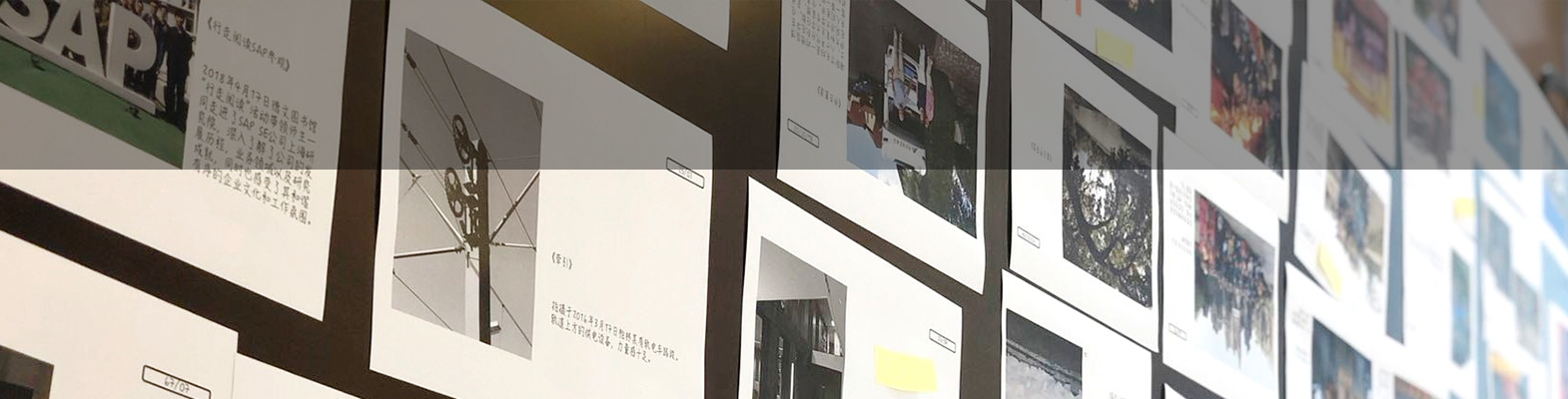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什么是艺术?与博伊斯的对话》中文版是根据德国乌哈豪斯出版社2011年第七版(7. Auflage 2011 Erschienen im Verlag Urachhaus)翻译而成。原书初版于1986年,这也正是博伊斯离世的那一年。至今已然30年,期间本书在德国已经再版七次,英译本(Published by Clairview London)从2004年至今也已再版过四次,足见本书是研究博伊斯艺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 图 / 韩子仲)
约瑟夫·博伊斯(1921-1986)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艺术家。赞誉者称博伊斯是继达·芬奇之后最伟大的艺术家,是他开创了艺术发展的新纪元;而批评者认为博伊斯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但无论怎样,正如前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院长吕佩尔茨所言,博伊斯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至今他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力。总体来说,博伊斯的艺术思想体现了自20世纪以来欧洲文化精英对于自身社会和文化发展模式,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深刻反思。博伊斯通过不知疲倦的创作、教学、演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有关于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献资料,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对“扩展的艺术”观念的实践。然而本书的重要性并非是在于对这些艺术概念的分析,而是着重于对博伊斯的“物质”观念和面向“事物”的态度的分析,这些内容在对话中都是建立在具体的物品、练习和作品上,而这些正是博伊斯所建立的新艺术哲学的基石。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份研究博伊斯艺术思想的最原始资料,是进入博伊斯艺术世界的一把钥匙,是解读博伊斯艺术作品的源代码。
虽然本书中的对话使用的是日常语言,而且博伊斯一直强调他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是非常一般,普遍的道理,但恰恰是这些日常语言在博伊斯这里往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想就其中的一些能够串联起博伊斯艺术思想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最重要的是博伊斯的“物质”(Substanz)观念,他之后形成的“社会雕塑”、“扩展的艺术”等等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博伊斯所说的“物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理性存在,但也绝非只是一个心理现象、意识图像或者是某个抽象的本质观念,它是一个能够在不同认识层面上把握到的,具有内在精神品质的整体概念。
我们可以结合博伊斯在谈话中所使用的另外两个词语来理解“物质”的意义,它们分别是“质料”(Stoff)和“事物”(Sache),这两个词也都有物质的意思,但博伊斯在对它们的使用上是有区别的。
“质料”(Stoff)是现实存在的物质材料,但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材料”(Material)那样笼统和宽泛,“质料”是有具体的“质”(Qualität)的构成。在他眼里,“质料”是一个“上手之物”,它体现了博伊斯所说的“物质”的实在性。“质料”是一个可以被经验直接把握到的存在,如果没有“质料”的存在,你就无法进入到“物质”的世界中,更无从谈及去领会那个内在的实质。“质料”代表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所谓“物质世界”(Stofflichkeit)就是这种多样性的集合,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构造,生长和衰亡。博伊斯所使用的蜡、油脂、毛毡等等就是这种“质料”,或者也可以说是某个具体的“感性材料”。然而,博伊斯在对话中又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物质” 并没有“质料” 那样的实在。
另一个词“事物”(Sache)是博伊斯在对话中反复强调的,它的意思偏重于“事情”,这也就是物中有事,那么究竟在“质料”内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博伊斯认为,这个“事情”就是物质内部自身的造型原则、发展方向、进化法则,他认为这也是由一个“态势”(Konstellation)所决定的。博伊斯在对话中有时会用“gelingen”(完成;达到预期目地的行为)来表示他完成了一件作品,或者说是一个事物的完成。他所认为的“完成”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进入到事物中的最终结果。博伊斯一直以“受难者”自居,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所说的话——“成了”。“成了”在里面意味着某种使命的必然。因此,“事物”不是被创造出来,“事物”原本就在那里,它需要你去进入,最终按照它正确的方向去实现它,最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事物”或者说“事情”“成了”。当你能感受到“事物”处在一个正确的“态势”中,那么它就会和你对话,并且告诉你在什么时候是完成了。
“质料”最终要以“事物”的方式被完成,而博伊斯所谓的“物质”恰恰可以被看作是这两者的统一。“物质”在博伊斯看来既是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存在,同时它又指向了某种内在的、精神的、超越性的“实质”(在原文中“实质”和“物质”都是用“Substanz”来表示的)。对于物质的把握,它都是首先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东西”(Ding)开始,以“质料”的方式为我们体验到,然后进入到“事物”中,认识到其中的“态势”,那么,它的形象就可以被理解为是这个具有内在精神的实质(物质)自身赋予形象的一个结果,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象征,符号,或者是神话和寓言。
然而,我们在这里区分出“质料”,“事物”,“物质”不同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恰恰相反,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层面上的表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物质”过程,既从“质料”到“事物”的实现,这本身也是一个超越性的认识过程。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精神自觉的过程,并且他能够在其中建立起自身的存在并实现超越。因此,对于“物质”的把握对博伊斯来说绝不是物理性的,或是建立在分析、综合的概念上的,而是对此所持有的一种本质直观的态度,一个思想的塑造过程。
其次,构成物质永恒运动的核心就是“态势”(Konstellation),在谈话中,博伊斯认为,“态势”是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事物发生的内在原因。Konstellation的意思是“形势,局势,事态”,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指“星座的位置”。它从词源上来说是由拉丁语“con”和“stella”构成的,意思是“天体的交汇”。它最初的意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占星术所指的“epoché”,意思是在一个星象图中天体运行轨迹中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是在运动中的那些临界点(Haltepunkt)(这也是博伊斯一直强调的“边界”)。“态势”或许有点类似中国人所说的“仪象”,而英译本的作者把它理解为“母体”(Matrix)。总的来说,博伊斯所谓的“态势”指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转瞬即逝的那些可被确定的点,当所有这些点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永恒运动的天象。它在每一个瞬间的定格,也是在可被确定的点上,用博伊斯的说法就是“凝固”或者“结晶”,一个具体的个性化形象就浮现出来,所谓万物由此而生。所以事物中存在的这个“态势”从总体上奠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某些东西的追问,它构成了博伊斯艺术问题的中心。
那么“态势”本身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特殊的定像?博伊斯在对话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尽管他认为皮亚琴察的铜肝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态势”图像的象征。然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态势”中包含了无数运动着的时间和空间的节点,对于每一个这样的节点来说,它们自身可能在某个瞬间产生确定的形象,但是当所有这些节点汇聚在一块,很难从整体上固定一个确定的形象,因为你无法想象它们都会在相同的瞬间同时保持不动。因此,虽然我们能够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中(时间和空间的节点)认识到“态势”,但“态势”本身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说,“态势”实际上意味了一个存在于任何物质中永恒的、绝对的运动。
因此,博伊斯是通过“两极”的扭转来呈现这种“态势”的永恒运动。比如热——冷;混乱——有序;非确定——确定;流动——结晶;正像——反像;生命——死亡。他把“两极”的关系归结在一个更高层次的关系中,任何强调单极的运动都是片面的,因而不能达到一个“事物”的理想状态。从上面提到的这些可以相互扭转的对立关系出发,博伊斯提出一个总体艺术的概念。在总体中,艺术和反艺术,科学与反科学都是对的。缺失,或者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因破坏平衡而导致发展上的问题。正如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反自然科学,艺术没有反艺术的加入将不可能继续发展。
在这个“态势”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博伊斯所说的“力”,它是和中世纪哲学中所谓的“actus”和“potential”相关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表达就是“实现”(Energeia)和“潜能”(Dynamis),即现实性与可能性。
博伊斯一直强调的“能量”(Energie),也就是来自“Energeia”,意思是“wirkende Kraft”,即是一种正在产生作用的力,或者说是一种正在“实现”的能量,它在博伊斯这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
“潜能”(Dynamis)意思是“vermögen,können”,意为可能的,有能力产生变化的力。博伊斯把它理解为“力的潜能”(Kräftpotential),是一种引而不发的“潜在的力”。每一个事物,即每一个被实现的能量,它同时也是为下一个发展阶段所贮备的潜能。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现实的存在并非只是一个终结,恰恰相反,它同样也是一个开端。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博伊斯把“确定的”的事物同时也理解为一种“超确定”的存在,因为在每一个“确定”的东西中都包含了开端与终结,成长和消亡,生命和死亡,它必然会超越自身而进入到一个更为辽阔的生命中。
博伊斯通过对于物质以及运动的研究来明确他艺术的终极目的,即:走向人的自由和创造。然而,读者会很自然地问到:既然如他所言,物质,或者说是事物已然将真理性的东西呈现出来了,那么我们人只需要去认识、遵从,或者说是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不就可以了吗?那在这其中还谈什么人的自由和创造呢?这也正是博伊斯在对话中需要解答的问题。
首先,从“对话的缘起”中的练习可以看出博伊斯并不认为存在着什么可以脱离了意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现象是无法脱离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进行的思维活动的,人也就是一个能量的接收器。在对于物的观察中,人会形成一种自我意识,由此而建立起自己的形象,这个过程同样也正是一个进入到“事物”中的过程,一个思的过程,一个精神自觉的过程,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事物”意义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有关于“人”自身的认识。那么,当人认识到了“事物”中存在的这种真理性,那么他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方向去行动,进而创造一个具有内在真理性的东西。博伊斯明确反对一种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他号召人们要积极地投身到“事物”中去,这不仅仅是认识的要求,还是自我塑造的要求,最终是创造的要求。这种对于人的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博伊斯认为很多“事物”之中的“差错”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它有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走坏,就像现代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一样,而只有人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去修正它,改造它,把它重新纳入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博伊斯在对话中反问对方:“难道你还认为人只能认识真理,而不能去创造真理吗?”
对于“自由”和“创造”的理解,博伊斯也反复强调了它们都不是一种任意而独断的行为,相反,它们只有建立在一种对规律和原则的认识上才能够实现。他认为当代社会对“自由”和“创造”的滥用,若不是出于某种生物性的本能,就是被某种完全违背“事物”本来样子的欲望结构所推动。因此,博伊斯认为“意志”是实现“自由”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唯有“意志”才有可能让你深入到“事物”中去,唯有“意志”才可能控制你的欲望,约束你的行为,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创造。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谓的“自由”正是某种“意志行为”,正如在《工作场的蜂蜜泵》这部作品中,博伊斯通过一个辊轴不断搅动油脂的设备来象征一种精神与欲望的缠斗。最终,意志获得了胜利。
无论是博伊斯从“物质”研究拓展出来的“社会雕塑”、“总体艺术”观念,还是他对政治(自由,权力),经济(资本的循环),精神生活(斯坦纳)的讨论都是他试图回归人的本质——自由,释放创造的努力,从而实现他改造社会的理想。他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一个“扩展的艺术”观念之中。
在这个“扩展的艺术”概念中,博伊斯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生产性。他认为,艺术应该成为所有生产活动的最初的生产(Urproduktion)。博伊斯认为,从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生产力,并且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权力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的繁荣;另一方面,物质的品质,尊严和意义也在这种“进步”中被损害,存在的问题已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过程中,被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束缚了人的自由。而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唯有将自由归还给人,才能释放出最大的生产力,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因此,博伊斯认为应该重新缔结劳动—艺术—自由的关系,恢复艺术的生产属性,而不是把艺术放在什么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中来讨论。艺术应该成为一种原初的生产力、一种真正的劳动,这样,它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正如编著者哈兰所言,博伊斯仍旧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他将自己的艺术深深地扎根在传统艺术的土壤中。博伊斯对于如今艺术家的批评主要在于,博伊斯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扩展的艺术”中的“边界”,而且缺乏对相应的责任的承担。任何现实发展的状态都是与那个在它边界之外的世界遥相呼应的,而那个边界之外的世界对于处在现实中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或者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担当此任。
通过以上对一些关键词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博伊斯的艺术思想基本还是延续了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他在对话中坚持把自己的艺术工作归为一种人类学的研究,由此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美学区别开来。博伊斯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试图从认识论的立场去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制定真理的标准;另一方面,他的物质观念又带有很强的本质主义,其中掺杂了大量神话、寓言、宗教的内容,这使得他的物质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他深受鲁道夫·斯坦纳的人智学的影响。所有这些让他的作品、行为看上去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在表达一个“普遍的真理”、一个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反而更像是一个艰难晦涩的文本,甚至是令人感到有些畏惧的仪式。博伊斯在不遗余力地鼓吹人的自由,创造力神话的同时,也将自己打造成公众的精神导师、在世的基督耶稣,这些无疑招来众多非议。
在所有对博伊斯的批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布赫罗(Benjiamin h.d.Buchloh)于1979 - 80年在纽约古根海姆举办的博伊斯回顾展期间所撰写的批评文章“偶像的黄昏——批评的预备文本” 。
布赫罗认为博伊斯通过那些精心设计的物件制造了一个所谓内在的、永恒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原型领域,而这正是他编织的个人和公众神话的基础,充满了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妄想。在所谓绝对开放的存在中,公众创造力的神话只会是在制造混乱。一个假冒基督的疯子,在这场混乱中臆想出他作为受难者的神圣而又崇高的使命。最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不过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艺术集权主义下的谎言。博伊斯鼓吹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化、政治生活的美学化,所有这些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性格特征。伟大的理想,神圣的使命,革命的狂欢,毁灭的快感,重生的迷狂,这些正是纳粹统治下给予人民的政治美学。
在身陷二战后迷惘的德国人看来,博伊斯通过对这种带有本质主义、神秘主义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复兴,以此来抵抗日益盛行的英美实用主义文化的入侵,将自己成功地包装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英雄。对于英美世界来说,自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自由,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制度、法规建立起来的;而博伊斯的自由是本质主义的、精神的、非制度化的,所以,博伊斯的自由事实上对传统、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是危险的。
布赫罗在文章中对博伊斯的批评是严厉的。直到今天,布赫罗对于这位自我神话的艺术家的批判仍然影响甚众。除了对博伊斯艺术中所流露出来的集权主义的担忧,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20世纪以来偏重语言形式研究的英美学界和坚持本质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学界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无论我们是认同博伊斯所指出的在技术统治下的现代文明的危机,还是把博伊斯本人看作是一个制造混乱、催生集权、毁坏艺术的危险分子,或许我们都可以引用荷尔德林在《帕特默斯——献给洪堡侯爵》开篇所写内容的作为结束:
神在咫尺,
难以把捉,
危险所在,
拯救者亦在成长。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首先要感谢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孙周兴先生。大约三年前,当我把这本书的部分译稿寄给他后,孙老师很快给我回复,并指出这是一本研究博伊斯的重要文献,当即决定将本书收录于他在商务印书馆所编的“未来艺术丛书”中,并帮我联系了出版社,这让我倍感鼓舞。后来在版权联系上遇到波折时,亦是在孙老师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达成。是故若没有孙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或许此书中文版的面世还会耽搁许久。同时,我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另外,我要感谢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雕塑家韩子健,他审阅了全部中文译稿,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错误,并就一些重要内容和我展开讨论。所以,本书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多年来我和他对艺术问题交流的结果。我还要感谢 Alanus Hochschule für Kunst und Gesellschaft 的学生张翀和他的导师 Prof. Jochen Breme,他们帮助我核对了博伊斯黑板画中的部分文字。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大学同学,现客居斯图加特的建筑师张小欧女士,以及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姜睿(Frau Jiang- Blumenhagen)。此外,这本书得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际项目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黎梦菲女士,感谢她多年来对于我的支持和鼓励。
本人学识有限,译文不当和错讹之处难免,企盼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诚如博伊斯所言,这是一次尝试,如若能激发更多有关于艺术问题的讨论,本书的初衷才能达成。
资料来源:原力设计,2017年7月14日
https://mp.weixin.qq.com/s/8fGVnHj56ek5Bxc5VfV9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