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德语作家群像中,赫尔曼·黑塞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名字之一。黑塞善于以细腻入微的笔触探查心灵世界,剖析人心中难以弥合的二元对立。人如何跨越自身天性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鸿沟,抵达自由和谐的彼岸——这是黑塞探索了一生的问题。而这个命题,无论对于他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还是对于当下的网络化社会,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变幻的世间万象中坚守内心的纯净,在浮躁的时代中寻找通往心灵之路,这既是文学的使命,也是一种生存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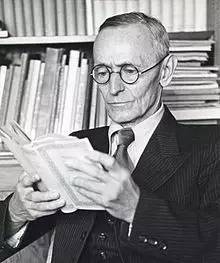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Hermann_Hesse
“面对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世界时,继续坚持骑士精神、相信魔法”。
这是德国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在1927年的《黑塞传》中对黑塞创作人生的总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将黑塞称为“20世纪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然而在写出这部传记之后不久,巴尔就因病去世,他并没有看到黑塞的《玻璃珠游戏》。如果巴尔能够陪伴黑塞走到最后,或许会重新斟酌这句评价。
回顾黑塞的一生,浪漫精神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篇章,但却不能概括其晚期的美学境界。正如《悉达多》中的那位贵族青年一样,对于这位作家,人生之路即是修行之路,他的每一段成长和蜕变,都被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天性与理性
1877年,黑塞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他从小被送入了莫尔布隆的神学院学习。然而充满虔信氛围的家庭和学校并未在这位少年心中孕育出信仰,相反,他走上了另一条朝圣之旅,这条路的尽头不是圣像,而是文学。
少年的黑塞内心充满愤怒。他的愿望是成为诗人。模仿浪漫主义风格创作充满梦幻的诗行,给他带来一种莫名的欣慰。然而拦在通往理想道路上的人,首先是自己的父亲,再往后似乎又是整个世界。在多次反抗家庭对于他“光辉前途”的安排之后,他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光明与黑暗的对立——这是少年时代的黑塞感受到的最深的矛盾。光明,来自于学校和家庭所宣扬的温和而刻板的市民人生,而黑暗,则是隐匿在课堂和圣歌背后的懵懂欲望,那是危险丛生的另一条道路。这种体验,正是酒神和日神精神的不断纠缠。黑塞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分裂,他既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同,又渴望以诗人的身份站在边缘。这种矛盾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渐渐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痛苦。
敏感的黑塞通过小说不断探讨这种天性和理性、自然与文化的断裂。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钦》中,他写了一位艺术家的人生故事,借助这个形象表达了自己对没有灵魂的市民社会的不满,提倡远离城市、回归自然。这部作品很快畅销,黑塞逐渐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在作品中提出一种治疗世界和个体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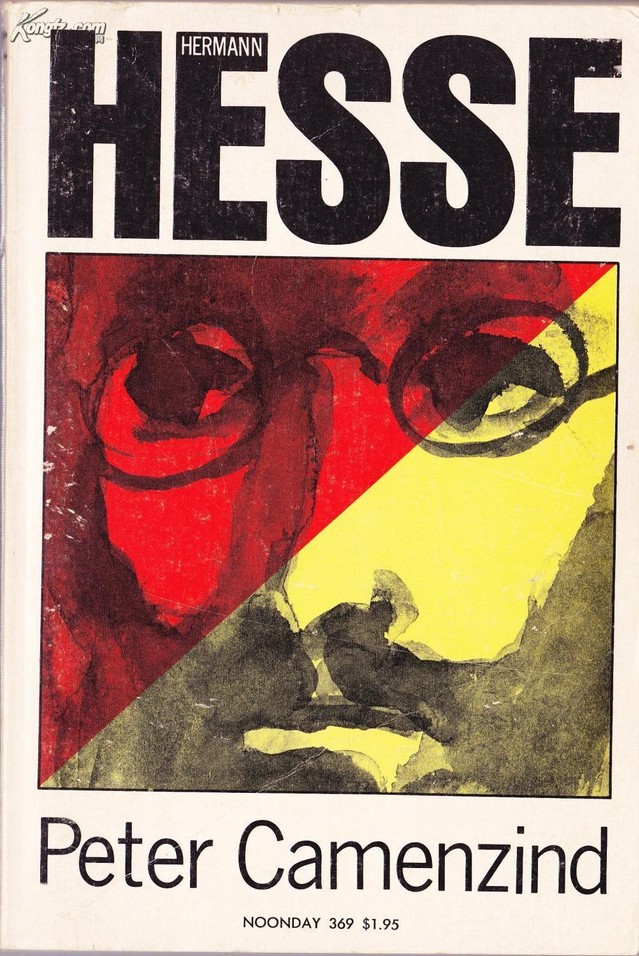
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15357_257049052/
黑塞经常用两个完全对立的形象来表现个体内心的挣扎。比如《在轮下》中的吉本拉特和海尔涅,以及《德米安》中的辛克莱和德米安。吉本拉特失去了敬仰的朋友,溺水而亡;辛克莱则接受了德米安的神秘启蒙,最终和德米安融为一体。在这些作品中,黑塞的个体理念逐渐清晰,他呼吁人坚守自己的内心,不要臣服于外在的权威或制度,接受自己内心的两极性。实现自我即是拯救世界——这就是黑塞的美学态度。
这种以实现自我为终极目标的个体主义,首先针对的是当时的市民文化。在黑塞看来,这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教育和文化方案,都是反人性的。当然,这种绝对的个体主义也为他招来了一些非议,在批评者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他沉湎于天性与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不能自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种对天性和内心的不断呼吁,才令黑塞成为20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读者遍及世界各地,在战后的美国,黑塞甚至成为了思想解放文化运动的偶像。

艺术与现实
黑塞是一个阅读涉猎非常广的人,他的思想土壤很复杂。除了少时非常喜欢的浪漫派文学,他也很熟悉欧洲的启蒙作品,尼采的酒神精神更是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观。除此之外,因为黑塞的祖父是传教士的关系,他从很早时就开始接触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在他的身上,东方的神秘整体观和西方的个体精神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1922年的小说《悉达多》。悉达多的确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作家以如此贴近东方的立场,讲述了一个关于内心修行的故事。
悉达多的人生轨迹是曲折的,黑塞让他先以沙门的身份拒绝世界,然后又以商人和恋人的身份重新走进世界,体验情欲和喧嚣。世界的真理并非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万千现象之中——这是悉达多修行的核心阶段,从纯粹的精神回归到具体的表象。最终,悉达多在一条河边悟道,他从河中看到了世界的过去和未来,看到了世间的千变万化,而这些形象最终又回归到他的心中。这是一次虚拟的悟道,黑塞借助东方的宗教和哲学理念,重新定义了一个绝对的“自我”概念。这个自我,并不是弃绝世界的唯心主义,相反,他把世界和个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揉成了一体,在这个新的个体中,肉体和精神已经不再敌对,世界即是自我,自我也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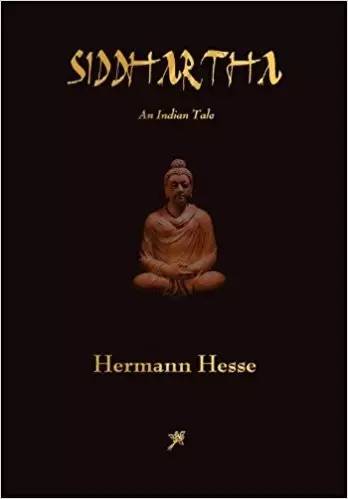
https://www.amazon.ca/Siddhartha-Hermann-Hesse/dp/1603865144
《悉达多》为黑塞思考的个体二元性提出了一种解救方案。然而,这仅仅是针对悉达多的方案。对于黑塞自己,疗伤依然没有结束。文坛的成功,虽然为黑塞带来了荣誉,却也加剧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之间徘徊两难的窘境。黑塞的中年生活并不轻松,他渴望爱情,却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对于生活的琐碎杂事,更是无从下手。荣格的精神分析,给黑塞提供了一种心灵治疗的方案,同时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在《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中,艺术家的生存危机被表达得淋漓尽致。黑塞的烦恼,是如何在不拒绝生活的同时远离生活,追求心灵的自由。所以,晚年的他选择了在瑞士田园隐居,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实现了自己早在《彼得·卡门钦》中所表达过的回归自然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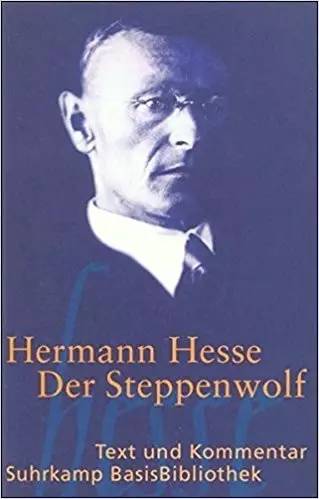
https://www.amazon.com/Luchterhand-Taschenbucher-Steppenwolf-Hesse-1999-10-31/
同东西哲学交融的《悉达多》相比,《荒原狼》类似于对同一问题所提出的另一种西式解读方案。在这部作品中,黑塞塑造了一个在生活和理想之间摇摆不定的艺术家形象。这个形象带有很强的自传性——黑塞一生都饱受这种双重选择的折磨。主人公哈勒尔是一个奇特的叛逆者,他抗拒主流,却又缺乏绝对的独立性。换言之,叛逆只是他用来争取一种有限的心灵自由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奇特的魔法剧院中,哈勒尔找到了实现自我的途径。在这个充满幻象的世界里,他肆意宣泄欲望,却最终意识到,通往自由心灵的道路,并不是完全听从内心驱使,而是接受世界和自我的两极性,在幽默和大笑中化解矛盾,不断接近终极的目标。这部充满荒诞和挑衅意味的作品呈现了黑塞晚年思想的转变,他已经不再沉迷于找到一种绝对的心灵自由之路,而是建议将艺术和生活的矛盾本身变成创作之源。
文学中的自由国度
黑塞虽然孜孜不倦地追求个体自由和心灵独立,却并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的避世者。在生前最后一篇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中,他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批判了希特勒领导的第三帝国。《玻璃珠游戏》是一部关于未来艺术乌托邦的小说,黑塞创造了一种终极艺术形式——玻璃珠游戏,将自己对纯净艺术世界的理想寄托在音乐当中。在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音乐中,人们能够找到一种终极的个性和表达方式。这是黑塞对当时笼罩在纳粹暴力政权下的德国的抗议。在玻璃珠游戏中,一切矛盾和对立都不复存在,个体既在集体之中,又有自我的位置。通往内心和自由的方式,是艺术。这也是黑塞对自己反复探究的问题所作出的最后一次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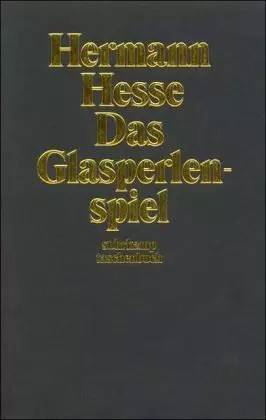
https://www.buecher.de/shop/buecher/das-glasperlenspiel/hesse-hermann/
1962年8月9日,黑塞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从早年的叛逆,到中年的彷徨,再到晚年的淡然,黑塞的人生轨迹是坎坷的,然而,在现实的坎坷中却绽放出了一朵永不褪色的文学之花。
(作者丁君君,女,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师)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外全球史,2017年9月1日
https://mp.weixin.qq.com/s/RUeuJ7qUwW_KQPyXNv0gh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