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金秋十月,是德国高校的开学季节。来自德国及世界各地的数十万名新生将在德国近400所各类高校注册入学,开始他们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学习。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关注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德本科生、现任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控制和自动化系统领域的教授、电气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永健在他们校刊上欢迎新生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他当年的求学之路,特地对他采访,希望他和我国年青一代学子们分享留学经验。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丁教授,您是同济校友,也是我国改开以后第一批留德本科生,是老前辈了,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年您的留学背景?
丁永健教授(以下简称“丁”):丁老前辈不敢当。我是教育部公派留德本科生第一期97人之一(总共派出三期本科生约300人),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德语学习后于1980年9月来到德国,当时21岁。我们这批人最小的当时还不到18岁,最大的也就23岁。我认为打开国门,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西方学习,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最高领导层为使国家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英明决策之一。
中心:您到达德国后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丁:文化休克。当年的中国刚刚从几十年的闭关锁国里走出来。由于信息不通,我们对西方知之甚少。虽然在预备部受过德国老师们的熏陶,但一旦身临其境,还是感到诸多的不适应。所幸我国使馆教育处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为我们在海德堡大学安排了为期4周的“适应过渡培训班“,否则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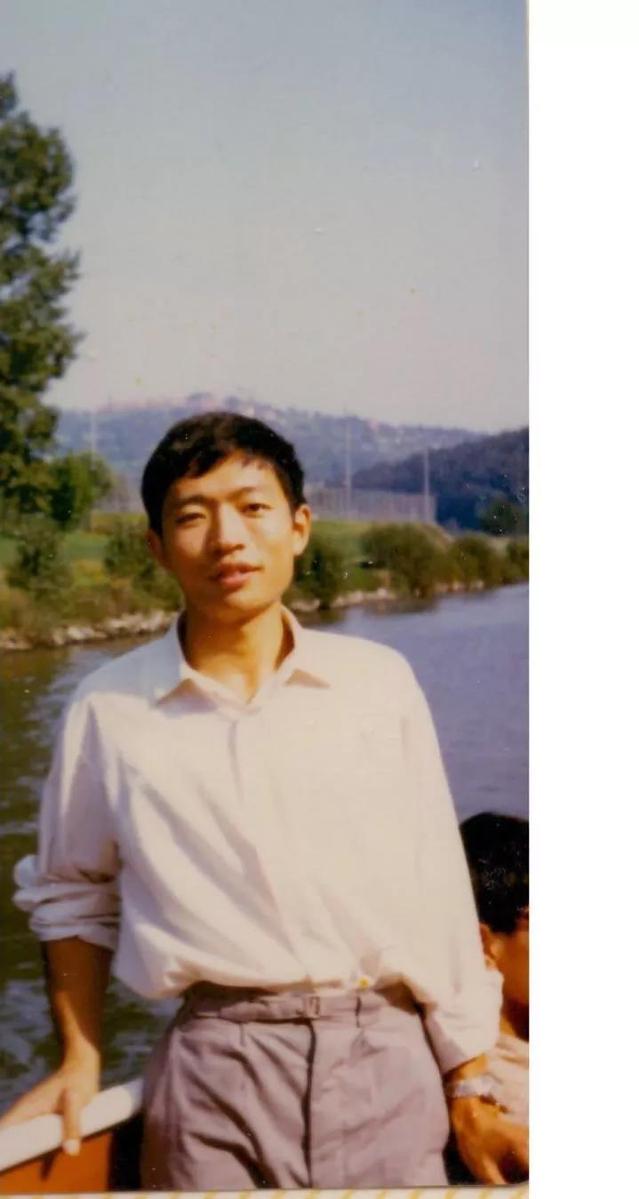
1980年刚到德国时在海德堡的Neckar河上乘坐游船
中心:过渡班都有哪些内容?
丁:从国情介绍到上街购物、开银行账号,到迪斯科舞厅,还有性启蒙课,五花八门。来到德国,辅导员们(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学生)陪我们去商店比较价格,学到了Aldi店同类产品(一般)比 Kaufhof便宜等等,使我们避免了许多弯路。要知道当年在国内,一支中华牙膏,全国一个价。
中心:您还记得大学开学的情况吗?
丁:当然记得。我们97人的学校和专业是教育部和DAAD及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商定的。我和其他九位同学被分到慕尼黑工大。我是电气工程专业。和我77年考入同济大学材料系完全两样,但我没有太多怨言。我小时候在我外婆家、一个苏北的小镇上长大,记忆中夏天为了让农民用水泵灌溉稻田,家里多次拉闸停电,我不得不在烛光下完成家庭作业,所以我知道电力对国家的重要性。
开学第一天的下午,系里学生会组织新老学生去学校附近一家啤酒馆聊天认识,我看大家都订啤酒,也来了一杯,结果那天我喝醉了(我在国内从未喝过酒),而且接连几天皮肤过敏。后来在巴伐利亚州时间长了,多次啤酒试验后终于脱敏。
中心:学了一年德语,您上课能听懂吗?
丁:我也碰到了和许多外国学生一样的难关:虽然上了一年的德语强化班,在上海通过了歌德学院中级2的考试,却仍然不能完全听懂大学课堂的内容。记忆最深的是上物理课时,教授口中讲“Kügeli”解释小球碰撞,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有同学从阶梯教室往下扔纸飞机。我不知道为何,就悄悄问旁边的同学,“他是普鲁士人吗“, 因为在上海听说过巴伐利亚人不喜欢普鲁士人。同学回答说,不是,他是瑞士人,刚刚把标准德语的Kugeln说成了瑞士方言Kügeli。类似误解,举不胜举。但我脸皮较厚,不怕犯错误,也乐意参加一些德国同学和社会上一些友好团体的活动,包括巴伐利亚村庄的民族服装俱乐部的表演晚会,差不多是两年以后,就能听懂一半以上的巴伐利亚方言了。
中心:德国老师、同学们对您们友好吗?
丁:在我那一级600多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中,只有五位来自神秘的东方中国。(同期被分到慕尼黑工大的其他五位中国同学分别是物理、机械和测量专业)。尽管一些德国学生对我们感到好奇,但一开始似乎较为谨慎地跟我们保持一定距离。后来在学期结束时一次大家认为较难的高等数学考试中,我和另一个中国学生拿到最高的1.0分(德国考试分为1-6分, 1分最高,6分最低)。在这件事被传开后,我记得有几位德国学生主动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学习小组。我们数学教授有个习惯,每年邀请考试成绩为1.0的同学去他的教研室吃他夫人烤的蛋糕。他特别好奇为何我的答卷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问我是否是“数学天才”, 要不要改学数学。我只好以实相告:在上海学德语前学过一年基础课,把当年习题集里几百条高数题目统统做过一遍。我也告诉他学习电工专业是国家的需要和我个人的愿望。
教授里面对我们最友好的是电子测量专业的S教授,他多次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组织学生们周末一起去爬山。通过他的课程考试后,S教授让我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实验,以此补贴生活费,因为我们从使馆拿到的比较拮据的奖学金(记得当时是每月不到600马克,包括房租、医保、交通、吃饭和零花钱)。那时中国外汇短缺,国家很穷,我们心怀感激,没有怨言。
中心:在学习之外的业余生活,您是如何融入德国社会的?
丁:那时慕尼黑的中国学生、学者不多,包括加兴(Garching)科学城的访问学者在内也不到100人。有些学生宿舍里只有一个中国人。某些专业也就一个中国学生。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德国同学们。有一些德国团体,比如汤若望协会和德中友协也常常和我们一起举办活动。
除此以外,对我锻炼较大的是参与组织中国学生会。记得那时慕尼黑有一个是以来自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为主的“华侨学生会“。他们得知我们到来,邀请我们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德国的结社法,但出于好奇,而且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仅参与了华侨学生会,并且被选入了理事会。第二年我甚至成为了学生会主席,并且把它改名为慕尼黑中国大学生和学者协会。记忆中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大陆学生的自治组织。使馆教育处没有反对,并且鼓励全德各地也陆续效仿。我和各位理事们一起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国庆和春节联欢晚会,以及郊游、参观等等。通过组织活动包括拉赞助和邀请校方及市里外办领导出席,不仅结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还锻炼了自己的演讲能力,也为后来在学术会议上、贸易博览会上和公司内部会议上做各种讲座报告、甚至是如今的大学课堂上讲课,都打下了一定基础。

1981年在慕尼黑学生会国庆晚会上致欢迎词
我从未因自己是一名外国学生而感到失落。作为一名华人,我时常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可能使周围的德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形象产生一种普遍印象。这对我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责任和挑战。我们在国外也多多少少地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在做着这件事。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学生学者及国内亲友传播德国文化、介绍德国工程技术。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是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学生互相交流的最大意义所在。
中心:您对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有哪些寄语?
丁:希望我的经历对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有所帮助。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希望留学生们把留学作为丰富自己人生、提高自己能力、扩大自己视野和促进中德友谊的极好机会,高高兴兴地来,顺顺利利地完成学业,再愉愉快快地回国发展或留下工作。祝大家成功!
中心:谢谢您的耐心留学生活介绍,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介绍您的职业生涯。
丁:谢谢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