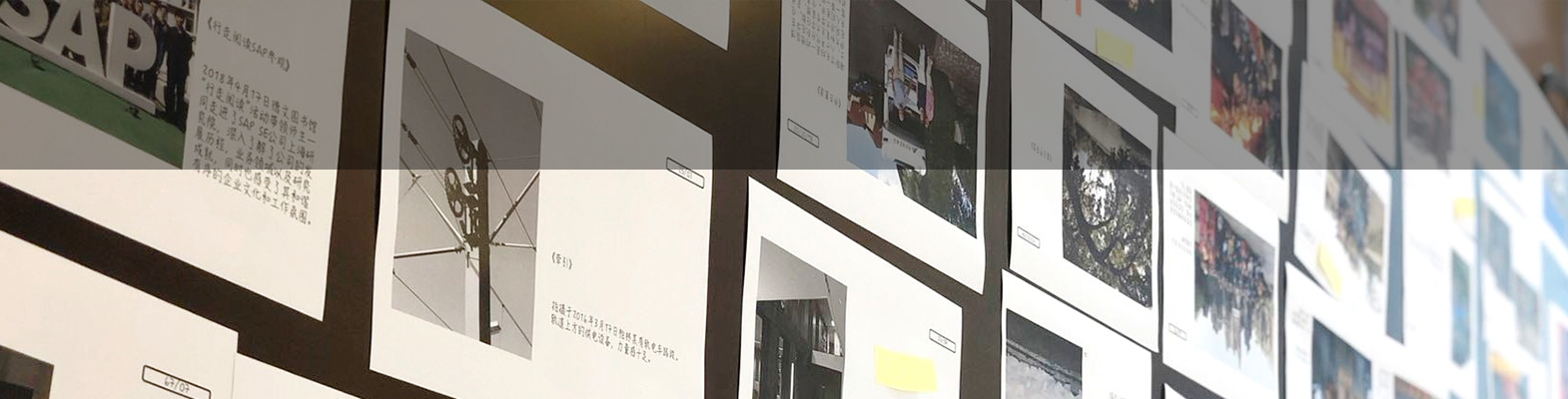2020年6月,来自匈牙利的德语作家、译者特雷西亚·莫拉的短篇小说集《外星人之恋》中文版面世。该书获得了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项目的支持,由丁娜译出,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也是这位德语文坛最高奖项——毕希纳奖得主的首部译介到中文的作品。

© 出版社提供
特雷西亚·莫拉
Terézia Mora
特雷西亚·莫拉(Terézia Mora),1971年出生于匈牙利的肖普朗,自1990年后长居柏林。其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被译成20多种文字,获奖无数,也是史上首位集齐毕希纳文学奖、德国图书奖、不来梅文学奖、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等最重要德语文学奖的女性作家,是德语文坛不容忽视的一个名字。
早在1999年,其处女作《怪事》引起文坛轰动,获得英格博格·巴赫曼奖;2013年,其小说《巨兽》获得德国图书奖;2017年,她凭借《外星人之恋》(2016年,慕尼黑Luchterhand出版社)赢得不来梅文学奖;2018年,莫拉及其全部作品被授予德语文坛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此外,她还是将匈牙利语作品译入德语的著名翻译家,译过当代匈牙利著名作家、被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的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代表作。
“ 特雷西娅·莫拉在她的小说和故事中,用心刻画了那些局外人,那些无家可归、无处谋生和无根无着的人,强烈而精准地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
——毕希纳文学奖评委
《外星人之恋》

[德] 特雷西亚·莫拉(Terézia Mora)著
丁娜 译
汉译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更多试读章节请滚动至本篇文章下方
《外星人之恋》是为莫拉赢得不来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十个短篇,如同十个特写,聚焦局外人生存窘境、直击时代痛点。书名中的 “外星人”并非实指来自外星之人,而是指那些徘徊在生活边缘的独行客与梦想家,那些平凡的“异类”、别扭的存在。
一次海边邂逅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一名夜班前台服务员暗恋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一位大学教师在逃避一段失败感情的同时也在逃避自我;一位日本教授爱上了一位女神……
特雷西亚·莫拉在《外星人之恋》中讲述了那些迷失却并未自我放弃的人们,那些仍然怀有希冀的失意者。他们是试图彼此靠近的陌生男女,不肯面对自己真实情感的孤独者。在这十个短篇中,莫拉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了那些似乎无处宣泄的情感,探索人们对友情、爱情和幸福的悲喜剧式的渴望。
该书译者丁娜是德语翻译界的一位重要译者。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居慕尼黑。主要译作有:《西方通史》(第一卷)、《应许之地》、《铁幕欧洲之新生》、《背对世界》《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德意志之魂》(合译)、《寻访行家》(合译)、《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合译)等。
“特雷西娅·莫拉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冷静而坚定的笔触描绘出心灵的全景。她的作品结构严谨,刻画着当代人的孤独和失落,那些点缀在日常中的短暂的快乐、对爱的渴望和不断的失败。她以强烈而富有节奏的语言,描绘了那些处于生存的转折点的人们。”
——不来梅文学奖评委
“特雷西娅·莫拉笔下的人物均非完人,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心早已破碎。这些被描述的生平犹如一篇篇记录,记载的是这些人的生活环境,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是存在压抑了他们,还是他们在任何事情能够发生之前就躲了起来?”
——德国《时代周报》
试读章节
以下文字选自《外星人之恋》中的小说
《往事并非如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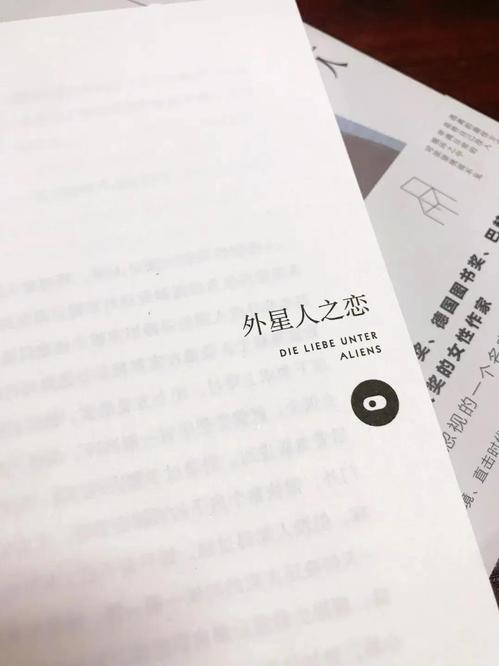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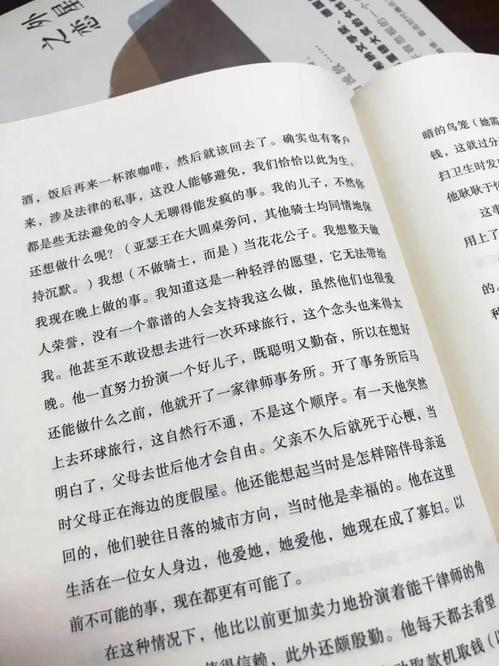
© 出版社提供
试读章节
以下文字选自
《外星人之恋》中的小说
《往事并非如烟》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我的心上人在同居八年后离开了我,因为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命根。这种话不能对任何人讲,我们的朋友们说。那时我离开了他们,并且再也没有回去过。
回到自己房间后,我打开了窗户,直到冷得要命,然后我又走了出去。
冬大衣太沉,也太厚。我走到金丝雀码头购物中心,找到一家廉价服装连锁店。没有青色的外套,但我找到一件浅褐色的。我又买了一件可以穿在外套里面的青色毛衣。我把旧的冬大衣装进购物袋拎了回来。蒙蒙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新外套的帽子上。若非手里提着购物袋,我现在看上去会年轻得多,像一件青色外套那么年轻。我好几次冲动得想把那袋子随便丢在哪儿,最后还是没丢。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天气不会再冷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如果人已经二十八岁了,那么八年就是一段不短的时光。起初我是个孩子,那时的事已经几乎记不起什么了;后来我上了中学,只记得常常暴走;此后又上了大学,住在佩斯(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由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城市布达和古布达以及东岸的城市佩斯合并而成。)的一间小屋里。我家乡的城市离首都足够近,可以每天两次坐丑陋、不准点并开得飞快的汽车往返。我家里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娇气,不能像其他数千名学生那样每天来回奔波,但最后他们还是卖掉一小块地(田产不能卖!),好供我买一间二十三平米的底层住房,这房子挨着一条大街,幸好是在后院,而不是前院。关于这条大街有一首美好的百年老诗,是赞美那里的椴树的,可惜现在城市交通破坏了那里的诗情画意。
G. ——大家,包括我,确实都只称他为“ Ge ”(注:前者为字母缩写,后者为发音。)——和我是在第一学期相识的。他是我们组唯一的男生,有些人认为他的长相配我绰绰有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人说话总是这么率直)。有个同事认为,他一定是个同性恋,因为他看上去很阴柔,而我则像个假小子。我们好了八年,从来没在一起住过。起初他住在父母那丑陋的新公寓里,他父母那时恰好要在芬兰待一年。我在那个公寓里住过一两次,睡在一张他青少年时期睡的床上,床是折叠镶嵌在一个组合柜中的。他父母回来后我就没去过那里。他常在我那儿过夜,但也会回父母家他的旧婴儿室,他把时间分配得井井有条。八年同居后,他用一个塑料袋就装走了放在我那里的全部用品。
在网上,我们还是朋友,所以我也不再更新什么。如今我去网上看了看,他也没更新。两具僵尸,我们在这方面也很般配。我不会去别的地方寻找他,我反正知道他在干什么:一切照旧。他不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是不想生活中继续有我。相反,我在看法里娅是否用真名或艺名有什么动作,都没有。能找到的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三首零散的诗歌。中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家综合大学报纸的技术员工(她会什么技术呢?还是这名称下的活完全不是我能想象的?)和另一家报纸的编辑。两年前她从网上消失了。她母亲去世的讣告也是在两年前,重病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悼念她的是她的孩子们和她母亲。这意味着:不知何时她与法里娅的继父和继子女们分手了。
据说法里娅在当服务员,Deviant Majority 就知道这么多。匈牙利的学者在国外常干这个。
上午阅读和写作,下午出去走走。如果我有什么强项,那就是建立常规。常规要有许多小小的修正,以便它们能把日常的单调维持在最小限度。最初,我的生活是在村里和小城市度过的,后来或多或少是在住宅和大学度过的,我先在大学念书,然后在那里工作。那段时间我只和唯一一个男人有过肌肤之亲。我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一样,去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安排的业余活动都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朋友练空手道,我喜欢看艺术影片。我按时呈交了博士论文,他延期一年,后来我对他说了那句话——他是我的命根,然后他就与我绝了交。我开始尽量不间断地在国外进行客座研究。第一站是德国,第二站是法国(在那儿我也常在河边散步),现在来到这里。
写作、散步、睡觉,这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没有所谓上课的负担,也没有所有其他作为一个人所应尽的义务,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如此看来,我目前的生存状况几乎如实验室般理想。有时我一连数日都想不起来自己还曾有过别样的生活。我非常善走——由于多年的训练,或是天生的。只有第一天我只走了两个小时,第二天起我就走四个小时了。四小时,走到摄政公园,再走回来。我在公园稍作逗留,观赏植物和我喜欢看的人。学生被带到公园进行体育活动。我一直看着他们,直到能分清他们:练倒立的丰满的黑皮肤姑娘,翻跟头的小个子金发女郎,谁球打得好,谁绳跳得好,谁能做后空翻。他们走后,我也打道回府。天黑时我回到校园,吃点晚餐,看看英国的电视剧。如果太无聊,我就去窗户那里看看大学生们,看他们如何去喝酒,然后再看他们怎样回来。此间不时会有火警警报,那我就出去,耐心等待消防部门允许我们返回自己的房间。我很少出门,因为我不喝酒,社交聚会和其他所谓休闲聚会很快就让我觉得怪异。
G. 也不喝酒,这就造成我们与其他人在酒馆里时只能坐一段时间,一旦他们的醉态令我们无法忍受,我们就告辞。囿于住房条件,我们无法在家招待很多客人,所以晚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两个人宅在家里。他听音乐,我读书。他不在我那儿的时候,我就去电影院,或在夜里去城里散步。我想念他,但我不说。我能够独处,如果不得已的话。我整个童年都是独自度过的。倘若我当初没说那句话,那我今天会在哪儿?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伊夫林喜欢喝葡萄酒,奥利偏爱啤酒。因为走着就能到(也就是便于离开),有一次我也参加了一个社交聚会。我自我介绍叫索菲娅(我不叫索菲娅,而是若菲奥,但这无关紧要)。“我现在在英德研究中心进行客座研究……”
“具体是翻译研究……”
但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我会说:
“荒诞派文学。”
或是“语言纯粹主义”。
或是“教科书中的异国话语”。
或是“英国电影中的德国人,英国男女同性恋电影中的不同德国人”。
我仅仅不说政治与文化,因为这是奥利的研究领域。
有一次我说自己研究门槛文学,后来发现对方理解成具体的门槛,也就是房屋内外的门槛。我们笑了起来。
当我到家时,消防队的人已经来过了。
六周以来,我一直在同一段路散步,总是沿着运河走来走去,我对这儿已了如指掌,哪怕再过十年我也不会对这里更为熟悉了。砖墙上的涂鸦和石头上的特色花纹,什么地方颜色浅,什么地方颜色深,有的砖比别处的更红。栏杆部分所画颜色的渐层,某些地方长的草与青苔,甚至有蜗牛壳和鸽子粪,确切地说是鸽子粪留下的某种痕迹。为什么想到六周能够等同于十年会令我安心,这我无法接受,但它就是如此。
现在天黑得越来越早了。慢跑者们下午跑步时就戴上了头灯,狗脖子上戴着同样会发光的项圈。如果天黑得早,那么下午、晚上或是夜里的区别就不大了。所以一次吃晚饭的时光,我还在卡姆登集市闲逛。一群开心的德国游客递给我炸薯条和苹果酒。可爱、显得年轻和衣着随便的退休者,他们怎么偏偏选中了我?而我为什么让别人选中?我可以说是为了测试一下自己的德语(我受到夸奖),但这大概不是真相。我不理解,但颇享受这种境遇:我开心地坐在他们中间,尽管他们大声喧闹、喝酒并搞怪,但与他们相遇仍属于我迄今最美好的经历之一。这些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正在想自己也许在做梦,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匈牙利语。我转过身:两名女服务生在聊天。我听不见她们在说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她们是匈牙利女人。我盯着她们,试图从她们的口型猜出她们在说什么,但不过是白费劲。能肯定的仅仅是:她们俩都不是法里娅。我站起身,大费周章地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好能继续偷听她们的对话——德国人嗓门大,为什么他们得大嗓门?——但那两位服务生不聊了。在洗手间我往镜子里看了看,我没法说别人是否能认出我。我脑门上有块疤,可并非所有人看人都看得这么仔细,并且日后还能记得。
第二天我醒后,首先想起的就是卡姆登的咖啡店,整个下午干活时,我念念不忘的都是那儿的咖啡。我知道是异想天开,可我就是无法打消那个念头,如果我再去那里,也许会碰到在别的时间段上班的法里娅。或者再次碰到些可爱的德国人。从现在起每天去:炸薯条、苹果酒、烟雾,他们讲述他们的家乡,我讲述我的。当然,我下午去那儿时,咖啡店空无一人,而且没有一个女服务生是法里娅。我在街上待了一会儿,转了转,从咖啡店到小酒馆。到处都能听到匈牙利语,大部分是年轻女子,其中一些也是女服务生,就是没有法里娅。我一直走,直到得在一个地铁站看看自己到底在哪儿。地铁很挤,为了忍受这种拥挤,我扫视众人的面孔,看有没有认识的,当然没有。有个男的在读一本翁加雷蒂(注:朱塞佩·翁加雷蒂 | Giuseppe Ungaretti,1888—1970,意大利实验诗歌流派隐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书,我差点儿与他搭讪,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发信息给 Deviant Majority ,问他有没有法里娅的联系方式。他许诺说去打听,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给我发消息的反而是在布达佩斯租我房子住的那个姑娘。我担心又发生了漏水事件或是暖气不热,我在这里又有什么办法呢?都不是,她只是告诉我她要搬出去了。这可是始料未及,不过她安慰我说,已经替我找好了接替她的房客,一个叫薇罗妮卡的。
房客的更换令我不安,也就没能再去咖啡店寻找匈牙利女子。我沿着运河走了回去,回到那从容不迫的平静生活中去,但它已经不再那么平静如意。
问题在于,我每天都有浑身使不完的劲。我们不该忘记的是,我在此是得工作的,但我在图书馆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散步四小时的日子早就结束了,现在每天至少走六小时,但也经常走八小时,我的腿还能继续走。我的鞋不是什么特别的鞋,但也是步行鞋,我的脚不疼,我以前穿过更差的鞋。六小时,这是十一公里的路,从麦尔安德到运河北部终结地小威尼斯,到那儿就没法继续沿河走了,所以我更喜欢往南走,走到格林尼治,有一次甚至走到了刘易舍姆。我差点儿在刘易舍姆过夜,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从那儿继续前行,但还是没这么做。我并非真正的漫游者,我不喜欢某天在一个地方开始,而在另一个地方结束。
由于我结束时必须回到起点,在我转身的瞬间,常常感到要忍受一种失败,而不是轻松或充满预期喜悦地为回家而高兴。我变得失去耐心,开始忙忙叨叨,这又会令我很快疲倦,以致我不知何时起不再健步行走,而是拖泥带水,这甚至让去程也索然无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决定不走回头路,最好一路向前,直到走不动为止,然后从那儿乘车返回。比起坐地铁,我更喜欢坐公交车。光着腿的女大学生们礼貌地让我先下,从汽车站到我住的公寓不到两百米,这段路我还能不显狼狈地走完。我坐电梯到二楼,然后奔向浴缸。如果躺在浴缸中时响起火警警报,我就直接堵住耳朵。
我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直接睡到十一点,此前什么事也不做。我在阅览室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戴上耳机。我什么也不听,只是让气流在我耳朵与耳机振膜间回荡,振膜形成的均匀噪音会被大多数人称作安静。当耳机下的汗变得令人太不舒服时,我就摘下耳机毫不犹豫地离开。这时往往还不到下午两点。
散步对思维有帮助,但这只在最初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有效。我思索着必须写下来的与工作有关的事,有时也能小有收获,可进度慢如蜗牛爬行。不知何故,我在最近的几个月变得很蠢。这意味着,实际上原因不言自明。令我惊奇与恼怒的是,这其中的机理如此简单。最初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里,我琢磨课题,若有微小结果,我就试着把它存储起来,直到我感到脑子麻木了。然后我就坐到公园的长椅上,能坐多久就坐多久,十分钟。我坐在长椅上端详着各种鸭子与鹅,它们在小池塘里和附近的绿地到处留下羽毛与粪便。我看着推婴儿车的母亲们,她们坐在小池塘和绿地附近。我也看慢跑者,根本不想G.。他就想过没有我的日子,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不想他,而是想,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责任全在我,并且为什么他们还直率地对我说:这一切只能赖你自己。他们的意见为什么能高度一致,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率真,为什么这意味着他们都不想理我了。我找不到答案,我只能自我怜悯,想到这儿我站起身,继续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资料来源: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2020年6月27日,作者:特雷西亚·莫拉。
https://mp.weixin.qq.com/s/Y1w0D5MhaA1sTpufLd0iLw?scene=25#wechat_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