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提问1:格林童话是德国非常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篇青蛙王子,有人就说里面那只被变成青蛙放逐的青蛙国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可能是指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分裂出的莱茵联邦,有人就讲这样的童话也反映了德国人历史中悲情的一面,我想问的是,德国人的童话和他们的神话是否都一样反映了德国人的历史,在他们民族性格塑造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呢?
黄燎宇:德国童话的起源很复杂。我是搞德国文学的。我们这个学科的中文名称叫日尔曼学,它诞生于浪漫派时代,一开始它以研究日尔曼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己任。德国童话也是德国浪漫派搞起来的。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明克勒这本书的一大缺憾是没有提德国浪漫派,没有分析浪漫派神话。德国浪漫派对于德国民族意识构建起到很大作用。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神话可谓携手并进,都产生于19世纪。在18世纪,在歌德、席勒的魏玛时代,德国人没有什么民族意识,他们谈世界大同,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有关德国是用文化统一起来的民族的论调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两德统一前,很多人就拿歌德时代说事儿,说德国不必在政治上统一。就是说,这成为当时一大批德国知识分子反对德国统一的重要论据。再说德国浪漫派。浪漫派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构德国的民族精神。前面说了,我们这个学科叫日尔曼学,严格讲相当于德国的国学。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研究国学。国学是假定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里面蕴藏着某种值得骄傲的、值得尊敬的民族精神。这是国学概念最重要的内涵,也是国学研究者的理论预设。当时去搜集民间童话的德国浪漫派也带着这个诉求,但常常事与愿违。你们王老师也说过,德国浪漫派满怀民族激情去采风,去收集民间童话,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却发现,好些童话都起源于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很难算德国文化遗产。所以童话拿来构建民族神话很困难的。
李维:这个书里讲的很清楚,神话首先要有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能是完全虚构的,必须得有真人真事作为基础。比如必须得有马丁·路德这个人,而且必须在什么地方待过,然后反对天主教。至于他把论纲钉在教堂大门门上的情节,现在史学界都知道,这是虚构出来的,但是这个故事必须得基于他反罗马天主教,必须得基于他想把基督教德意志化,在当时造成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他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人物,这个时候才能有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完全脱离事实不行,但是一定会在原来史实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这是第一。
第二神话必须得有自己的具体地点,比如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地点在瓦特堡,这个地方今天还可以看到。地点可以实现历史的可造访性,就是你回到了这个地点,这个地点真的发生了那个事情,你到了这个地方觉得有神圣感,回归历史了,这些都是神话的基本特征。当然神话必须生动,必须传神,在有关路德的神话里,说他在瓦特堡的房间里碰到魔鬼,用墨水瓶砸向它,因此墙壁上还留下了墨迹,至今可见,这当然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大肆的渲染。
还有神话必须得有具像物,你所传承、你所尊敬、你所崇拜的,你想用它来凝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力量的,必须得有具体的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是个负面的例子,我十一期间带着学生教学实习到了旅顺口军港附近有个高地,叫203高地,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旅顺港全部情况。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和俄国的军队在这个地方厮杀,203高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神话,为什么成为神话?这个地方的史实是争夺战略高地,因为夺下这个高地以后,日本就可以在这个高地上设立观察所,然后引导榴弹炮轰击港口里的俄国舰队,所以双方在这个地方使出了最后的气力,日本人死了一万多人,那个高地有多大?就跟这个大厅差不多大。那个山有多高?大概就是8—10层楼小土坡,死了那么多人,日本死伤一万多,沙皇俄国死了大概四五千人,如果战后不在上面盖一个所谓的尔灵山塔,人们是很难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日本有一个将军叫乃木希典,一个侵华的急先锋,他当时把203改成叫尔灵山,他中文非常好,而且在上面树立了一个尔灵山塔,这个塔就是一个具像。现在每年都有日本人,其中有不少当年战死的日本兵的家属跑到这个地方来吊唁。我跟学生讲,如果没有这个塔,这个地方就是荒山包,谁也不会记得这个地方,就是死再多的人也不会记得。这个塔就成了神话的要素之一。这个塔下面的山坡上,就是当时日本将领乃木希典儿子战死的地方,现在也有一个碑,这些东西到底保留不保留,国内舆论界到今天都有不同声音。我只是告诉你,作为政治神话,从日本方面来讲,这个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除了具像物,还要用文学作品承载、体现故事,特别要上升到诗歌的高度。比如乃木希典当时记载战争用了两句汉诗,他说:“铁血覆山山形改”,就是日本兵死的太多了,尸山血河,整个山的形状都改变了,是尸体摞尸体,后面一句是“万人齐仰尔灵山”。“203”和“尔灵山”以至于成了日语当中的口头禅,日语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口头禅:“还能比203更难吗?”这就是他的神话,神话是什么?有故事、有具像物、有诗歌,有口口相传这就构成了神话。当然这个从政治上我们绝对是要批判的,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理解神话的产生。
比如说莱茵河的罗蕾莱神话都是有具体地点,到那告诉你就这儿,那个仙女就在这个崖上坐着呢,他都要有非常具体的地点。
黄燎宇:书里多次提到一个人,就是扬·阿斯曼。他的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阿斯曼夫妇都是做文化记忆的,他们属于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其实,神话问题也可以当成文化记忆问题来研究。你刚才说的这种神话,按照他们的设想,其实也是给我们留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民族神话不能仅仅存在于书本当中。你得把它外在化、形象化,甚至巨型艺术化。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只有这样,神话才能化为民族记忆、历史记忆或者文化记忆。这个事情做起来也很难。我们需要保留哪些记忆?我们需要凸显哪些记忆?人们肯定意见不一,肯定要争论。这位同学你可能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你歪打正着。这本书本来谈的是神话,但是里面一大段谈海涅,谈到海涅点评德国历史神话的著名的作品,那个作品就叫《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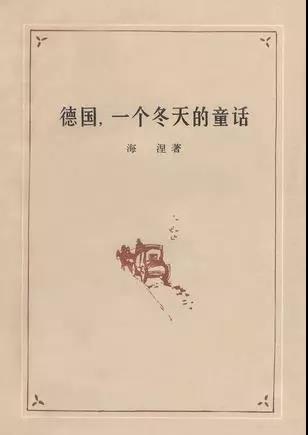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提问2:您说过每个国家有国家的道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道路在里面,所以我想问德国这个所谓的神话对国家道路选择有没有一定的指导或者有没有影响?历史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抽象的内核在影响着德国国家的走向或者神话的发展?
李维:我简单说一说,我特别想听黄老师的看法。
德国怎么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特殊道路?我觉得这个在德国史学界都存在着争论,因为文化是相对的,当有一个文化发展起来之后,它的力量变大,影响其他文化的时候,它就要把自己说成是普遍的道路,把和他不同的道路,一些所谓旁支的道路理解成特殊的道路。其实你想一想,天底下哪个国家的道路不是自己的,哪个国家的道路不是特殊的。所以如果在德国争论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从学术上来讲这是伪命题,我不是说你的问题是伪命题。因为每个国家的道路都是具体的,无非是和影响力最大那个国家的道路不一样,就被扣上特殊道路的帽子,而那个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又要把自己说成是最普遍的。
如果从怎么样理解德国历史的道路来讲,我觉得刚才黄老师刚才提的很好,这也是这本书呈现出来的线索,由于在战后对德国历史的反思出现的矫枉过正,把德国的历史说成是一个侵略的历史,特别是把纳粹和普鲁士混为一谈,其实真正消灭普鲁士的就是纳粹,就是希特勒本人,因为普鲁士代表的是贵族统治,希特勒讲民族社会主义。如果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讲,从赫尔曼之战开始,那个时候他们反对的是罗马帝国的压迫,马丁·路德反对的是南方天主教的权威,然后这里讲魏玛时期神话的产生是针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然后到了德意志帝国时期建立的时候,先打败了东南方的奥地利,再把西边的法国打败了,用铁血打出来的。所以如果从这部书里看它的历史,会呈现出一条线索,德国到1871年的历史是反抗的历史,不是侵略的历史。因为我们今天只是结合这个书来谈这个事情,这个话题非常大,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
黄燎宇: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德意志特殊道路是一个关涉德国历史的大问题。提这个问题之前你必须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否存在?刚才李老师已经说了,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特殊,事实如此。第二,假如说有这么一条特殊的道路存在,它是一条正道还是一条歪道?这就是价值判断了。而且,做这一价值判断就像我们回答德国历史悲剧的偶因论和必然论一样,总是后者占上风。现在认为德国历史悲剧必然要发生的观点总是占上风的,同样地,对特殊道路的否定也占上风。德意志特殊道路什么意思?应该从哪儿开始说?所谓德意志特殊道路,这其实是一个委婉表达,它是指德国历史走了一条歪路。有歪路就有正道。正道是什么?按照现代西方政治学话语,正道就在西面,而且是越朝西走越正确。我说的是德国的西面。现在既然要回答你问题,我想说点大家不经常说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的是,德国一开始就走了歪路,德国人是一个迟到的民族。这个迟到,指的不是德国人瓜分殖民地来晚了。它讲的是德国人在政治上迟到,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学到,尤其是人道思想。所以最后犯错误。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点我跟一些德国学者私底下交流时听到的话。私底下交流的时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些心里话。德国历史、德国文化里面当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不能因为出了个希特勒就全部抹杀。我们得具体探讨德国文化传统中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肯定的。譬如,这本书提到德国文化里面有绿色基因,提到他们几乎古已有之的环保意识。第148页讲到一个德国林业顾问,他在1923年写了一本小册子来阐释德国人的忠诚与森林的关系。他还在书中写道:“有个现象并非偶然:在我们德意志人的土地上,哪里有不毛之地,哪里的森林因为变成木材加工厂而索然无味,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就在哪里迅猛传播,大行其道。”对于这个林业顾问来说,布尔什维克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我们也知道,浪漫派时期即19世纪初,德国人已经在大谈森林的重要,大谈如何保护森林。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点,我甚至认为“浪漫”这个词不符合德国国情。我们知道浪漫二字是外来语,是音译过来的。我们中国人普遍觉得这是很棒的翻译,因为浪漫二字都有三点水,水边多浪漫!何况英国浪漫派就诞生在水边的,史称湖畔诗人。德国浪漫派的人间仙境可不是在水边,而是在林子里。我经常说最能体现德国民族精神特别是浪漫精神的乐器是圆号。圆号使人联想到森林,德语里也叫森林圆号(Waldhorn)。有意思的是,英语世界有一阵也叫它French Horn即法国圆号。总之,德国人的绿色基因没变过,纳粹德国也继承了这种绿色基因。你看看纳粹德国怎么修高速公路就明白了。纳粹德国修高速公路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如何把对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而且要考虑如何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驾驶员时时刻刻看见绿水青山。
德国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个基因,我们可以叫它红色基因。众所周知,德国经济不仅搞这么好,而且和英美的经济模式有明显差别。人们都说德国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我不是搞经济学的,我从语言和修辞的角度去思考,就觉得这个概念有一种逆喻效果,能够对人的常识产生刺激:市场就是市场,怎么又来社会关怀?社会思维与市场经济,这本来是水火不交融的,但是德国人偏偏要搞这个东西。对于这红色基因,我们不用追溯很远,看看德意志第二帝国就行。德国人对下层、对无产者的关注和关注始于第二帝国,所以他们的社会支出远超英法。德国近代史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社会革命。这一方面要归咎于德国人缺乏革命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懂得或者没有勇气把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许是德国人特有的社会关怀缓解了阶级矛盾或者说社会矛盾。换言之,和谐也可以纳入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范围。我们谈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时候,免不了要谈普鲁士。严格讲,德意志特殊道路就是普鲁士带领德国走的道路。而普鲁士的辉煌体现在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创建了德意志民族空前绝后的百年辉煌。当然也有人说威廉二世也是为希特勒铺路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一脉相承。如果这一说法成立,肯定就把德意志第二帝国全盘否了。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办公室里挂着那幅题为《谁是野蛮人?》招贴画,就是为了让大家随时思考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2017年11月28日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1670?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