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永健教授,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及终身教授。1978年2月考入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1979年转入同济200人德语班,稍后转入教育部在同济大学开设的留德预备部接受德语培训,于1980年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并获证书硕士(Diplom)和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GRS、西门子发电部和意昂电力公司工作达17年之久,后于2002年被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聘为工业自动化教授,并多年担任电气工程所所长、工程与工业设计系副系主任。他还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分会(RSK-EE)委员、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司库和德国逸远教育与慈善基金会副会长等职。
采访人:蔡琳博士,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惟孔德馨》专栏主编。图片由被采访人提供。
蔡:丁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高票当选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的副校长!之前慕尼黑工大的孟立秋教授也曾任该校的副校长,您算是全德华人里的第二位,也是目前唯一在任的华人副校长吧?您能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遴选过程吗?或者另一个问法:作为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您是如何在侯选人中脱颖而出,竞争到这个职位的?
丁:谢谢蔡院长的关注和祝贺!据我所知,现任埃森-杜伊斯堡大学的丁先春教授也曾经担任过Senftenberg 应用科学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也不能肯定目前没有其他大陆背景的学者在德国高校担任领导职务,毕竟全德国有400多所各类高校。我们有个华人教授学会GDPCH,现有大约50名会员,估计覆盖了80%以上的德国华人教授,目前似乎没有人担任校长、副校长。
其实在德国许多优秀教授是不喜欢担任行政职务的,更别说全职或半职的校级领导,事务繁杂、影响专业发展、个人获利不多,尤其当任期满届不能连任、返回研究所教学科研岗位以后,会比较累人。当然作为学校的“招牌“,校务委员会(由全校教授、职工和学生代表组成)一般也不会让太年轻的教授们担此重任。我校的章程是每四年选举一次,一位校长,三位副校长(教学兼国际合作、科研兼技术转让和学校发展兼公关),采用校长负责制,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校务委员会确认。我在学校工作16年,当过8年电气工程所所长、5年工程与工业设计系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也许大家对我比较了解,而且确实我的为人有点“中庸之道“、“和为贵“,没有遇到反对票。当时16票赞成,一票弃权。
蔡:您太谦虚了。教授是否愿意出任行政职务确实是个人选择,而能否被推举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是依靠实力和口碑的。我很想知道校长提名您任副校长,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她做过相关陈述吧?
丁:其实这是校长第二次邀请我和她搭档。第一次因为家人身体有恙我推辞了,这一次没有理由再推辞。她挑选我估计是以下因素:第一她是从事文科的,希望工科配合;第二她了解我对国际合作感兴趣,也有经验;第三她知道我比较直率,不搞“阴谋诡计”,这也是重要的考量。
蔡:您将分管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和国际事务。您打算采取哪些策略来提高这所大学的教学水准及国际化水平?
丁:我将于4月1号就任新职,一直奉行”不在其位不谋政”的原则。按德国惯例具体打算是上任100天后再做汇报的。不过您是老朋友,所以提前汇报一下我的想法也无妨:我校有50多个学士、硕士专业,覆盖机电、土木、环境保护、安全工程、经济和企业管理、社会工作管理、传媒及翻译、幼儿教育管理和康复心理学等专业。在校全日制学生6000多名,约150名教授,200名其他职工,其中包括数十名短期科研人员和与综合性大学比如马格德堡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德国基本法保证了教授们(在公立大学一般都是终身公务员)的教学和科研自由,校长和部长也不得(内容上)干预。所以我做所长和副系主任时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最好的校长是“不烦教授的校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现在换了板凳,必须让你们烦心了。具体说如何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作为自动化专业教授我觉得目前确实是个好时机:即如何利用整个社会和工业界的“全盘数字化”(total digitization)转型,组织学校资源比如现有的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高校教学法研究中心,引进一些新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包括整个教学过程的电子管理,等等。另外一个工作重点是提高学生人数,主要由于德国东部地区出生率下降迅速,国内生源枯竭,所以需要优质的国外生源。
在国际化方面,我校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委托,若干年来牵头承办德国约旦联合大学GJU,成绩显著。由于资源集中投入约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学生交流受到一些影响。我希望能够在不影响约旦项目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其他国家比如东欧及亚洲各国的学生交流。由于语言的因素,德国高校在国际优秀生源竞争中不占优势,而应用型大学又比综合型大学国际知名度低许多,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颖的路径,比如和中国合作时,计划考虑对国内211高校学生和一些质量有保证的合作伙伴院校学生开通入学申请快车道(fast lane), 等等。
蔡:您在中国同济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工大均求学过,这两所都是精英型工科大学,您同时长期担任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的教授。您能否就综合性大学及应用科技大学做一个简单的中德对比?
丁:这个话题可以专门采访一次。中德教育交流这么多年,国内许多同行似乎还是对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本科及硕士培养以及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本、硕、博士培养体制,多有误解。举个例子,三分之二的德国工程师是我们应用型大学培养的。工业界需要的实用型工程人员数量,远远高于偏重理论的(纯)研究型人才。我们的绝大多数学士、硕士论文都是在企业完成的(双重辅导),目的是确保学生离开学校时就具备较高的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受聘工业界后立刻或较快胜任工程师岗位。这方面中国国内即使是一流高校也不易做到,二流高校毕业生许多就业岗位的专业知识需求实际上还不如德国的技工,浪费了许多教育资源。好在教育部和各级教育部门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最近几年在强调一批地方院校的“应用型转型“。当然我知道这事不容易,“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理念转型,家长和学生的理念改变和成长模式的多样化(改变“高考独木桥“),以及工业界的配合(不仅仅是依靠政府花大量资金建设部分脱离实际的“实训基地“,而是让学生投入到生产和技术革新第一线去磨练真本领),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方面也是我今后愿意为我的祖籍国出力的核心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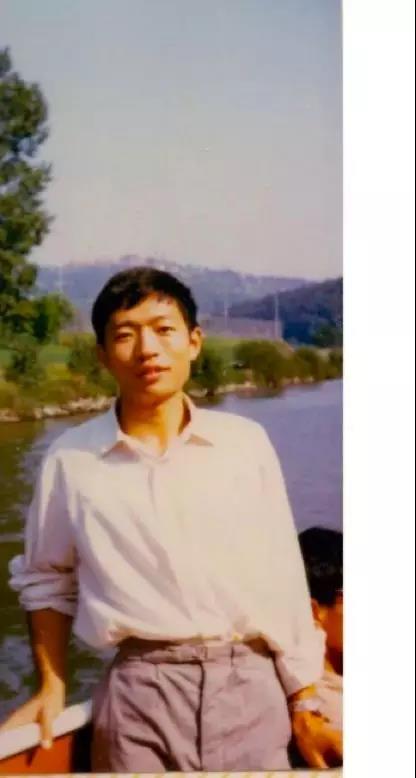
蔡:您个人的职业经历非常丰富,在工业界及学界均有建树。能否介绍一下您的重要的职场经验?是否也曾面临过岔路口或者重要的转折点?您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丁:一个快60岁的老人,必定经历丰富。不过我在大学毕业后至拿到教职前在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和意昂电力公司有工作17年的经验,在德国教授里也算是比较长的。我认为德国高校招聘工科教授时喜欢优先从工业界得到专业和管理能力较强的候选人,是德国工科人才世界领先的秘诀之一。职场道路因人而异,成功标准也不唯一。我的关键教训是当年在慕尼黑工大Diplom毕业时选了核电领域做博士论文,博士毕业时得到西门子公司两个岗位,一个是发电部的核电安全仪控项目工程师(在研究所参与了西门子数字化安全仪控系统TXS的开发认证),一个是程控交换机的中国市场营销经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从德国引进的第一个程控交换机EWSD的谈判是我在学生时代做的翻译,认识几个高层管理人员)。当时前苏联的切诺贝尔核电事故已经发生,大家对核电前景都不看好,那是一个继续攀登高峰还是彻底改行的决定,我选择了前者,总觉得搞专业比较踏实,没想到德国政府后来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果真放弃了核电,影响了我的部分专业发挥,而且到了高校以后这么多年,也许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专业,做好管理工作。不过我手中尚有德国经济部BMWi和教育与科研部BMBF的项目尚未结题,还需要双重辛苦几年,直到退休。
蔡:除了任职于大学,从事教学及科研以外,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并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您能否谈谈从事这些公益性事务的初衷是什么?
丁:除了在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担任司库(财务理事),我的主要公益兼职是德国逸远教育与慈善基金会副主席。后者是由一对当年共同公费留德的华人企业家同学夫妇出资为主、在部分老师、同学们支持下,以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学生为主的按照德国法律注册的基金会。德国的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数以万计,一般享有税收优惠,也是一种公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府不愿管或无力管的关注国内外社会弱势群体、环境及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式。我们80年代初留学德国的几批本科生除了回国工作或移居他国,留在德国的大多数同学已经入籍定居,对德国社会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同时也感觉到对当年国家资助我们留学的回报义务,和对国内一些贫困地区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山区或农民工的孩子们的同情。同学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我属于后者。除此之外,也有国内一些友好学校聘请我做客座教授,说实话,德国教授的兼职自由度比美国教授们小多了,主要是时间上不允许,我时常是力不从心。

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丁永健教授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发言
蔡:2017年中德建交45周年。中德之间建立了广泛坚实的交流机制,比如总理层面的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德工业界的合作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德高校研究所合作成立研究机构,设立双学位等,同时还有大量的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往来。一方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交流成果,但另一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误解。您作为一个跨越中德社会与文化的跨界人,您分析这种不信任和误解的根源在哪,您对消除误解有何建设性意见?
丁:对这个问题我比较乐观,对比起中美关系里的种种误解,中德关系里面没有惊涛骇浪。中德建交以来,大量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受到了良好的免费高等教育,许多优秀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服务,出了多位国家级、部长级领导和许多院士、教授,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奋起直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德国大批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也获利不少(当然也为中国创造了许多就业位置)。德国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也是相对开放的。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大量中资参股或收购德国优秀企业,比如库卡机器人、戴姆勒公司等的案例,德国舆论里有些担忧或不友好的声音丝毫不奇怪,一点也不会影响两国合作共赢的局面。中德两国没有直接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工业结构互补性强,这种长期互赢合作关系也符合广大在德华人及留学生的利益。所以我希望中国留学生不管是回国工作或者在德国定居,都要讲好中德友谊的美好故事,起到和老一辈学者们比如蔡元培、李国豪、裘法祖或者新一代的万钢部长等的桥梁作用。
蔡:德国教育与科研部(BMBF)提出的“中国战略2015-2020” 是基于中德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密和广泛的科学研究与教育合作现状,并注意到中国在工业与科技的某些领域已列于世界前列。希望巩固合作基础,也寄希望于德国的同行进一步参与到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创新领域的合作项目中来。为此德国教育与科研部已经资助了第一批以德国高校为平台的“中国能力建设”项目。您怎么评价“中国战略2015-2020”?中德高校在此有哪些合作发展机遇?
丁:中德的经济文化合作,离不开人员交流的师生合作。德国教育与科研部和中国科技部的战略伙伴计划对两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了极好的合作平台。我本人和团队也申请并获批了一个中德工业4.0 的”2+2”合作项目,计划下月启动。工业4.0离不开企业参与,所以”2+2”模式很有意义,具体如何进行和效果怎样还有待摸索。至于BMBF的“中国能力建设”项目,很遗憾的是我们学校虽然开过筹备会,但最终没有申请参与。这次对我的任命也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吧。
蔡:您入选副校长对广大留德学子而言是个极为正能量的励志故事!但所有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一步来之不易。您一定也经历过初来乍到的文化休克:您是如何克服语言、文化隔阂,克服心理上的孤单来适应环境,打开外来文化/社会的这一扇门的?
丁:这又是一个大的话题,去年10月份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就这一话题采访过我(回顾:留学德国是我人生的机遇和挑战——专访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德本科生丁永健教授)。总体来说,我似乎觉得现在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比我们那时对德国的好奇心小了,和德国同学交往能力/愿望似乎也弱了,常常为一点不顺心小事对德国社会“上纲上线”。我还是建议大家除了认真学好专业以外,多多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也包括对德国和欧洲社会的了解。我们不需要放弃中国特色、照搬德国的一切,但德国毕竟是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有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公民社会和福利保障体系,而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速度惊人,但毕竟尚未成熟,需要借鉴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反之,德国也在关注和借鉴中国的发展,尤其国家战略层面比如一带一路或非洲发展合作经验。

1982年作为慕尼黑工大中国学生会主席在国庆晚会上发言

2017年丁永健教授探望同济大学创始人宝隆先生的外孙女奥斯瓦尔德-托特勒博士(Dr. Erehelga-O´Swald Treutler)
蔡:我有幸认识您的家人。您有一个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太太开中医诊所,儿女都非常优秀,且全面发展。您是如何平衡中德教育观的,以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丁:我太太是江西医学院毕业后来德国深造并获得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的,她的诊所是中西医结合诊所。孩子一个在慕尼黑做企业咨询工作,一个在柏林医学院读书。用句中国话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根本不需要比,如果一定要比,我和他们说过要和父母比。作为华二代,他们有理由比我们第一代留学生移民走得更远。不过我不属于虎爸类型,比较宽松,我也和他们说过万一你们超不过我们,也不可怕,能生活得幸福即可。女儿这几周正在国内旅游,从去南京看望奶奶、拜谒中山陵到去成都看熊猫、去西安看兵马俑、再去北京爬长城,不亦乐乎。他们中文口语没有问题,但阅读尤其手写汉字不太过关,毕竟是黄皮肤的德国孩子,就原谅和理解他们的难处吧。记得儿子读大学时去苏州Bosch公司实习几个月,回来高兴地说起他和其他几个德国实习生一起去北京参观了“长墙” (= great wall), 我脑筋急转弯后说理解了,中国官方翻译叫长城,没有你的翻译准确。
蔡:丁教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作者介绍
蔡琳,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同济大学建筑学本科,2002-2010年求学于柏林工业大学“规划建筑环境”系,获工学博士学位。2006及2009年任德国GTZ机构(目前更名为GIZ)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江苏扬州、广西百色)项目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德城市更新比较、中德跨文化交际、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中德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