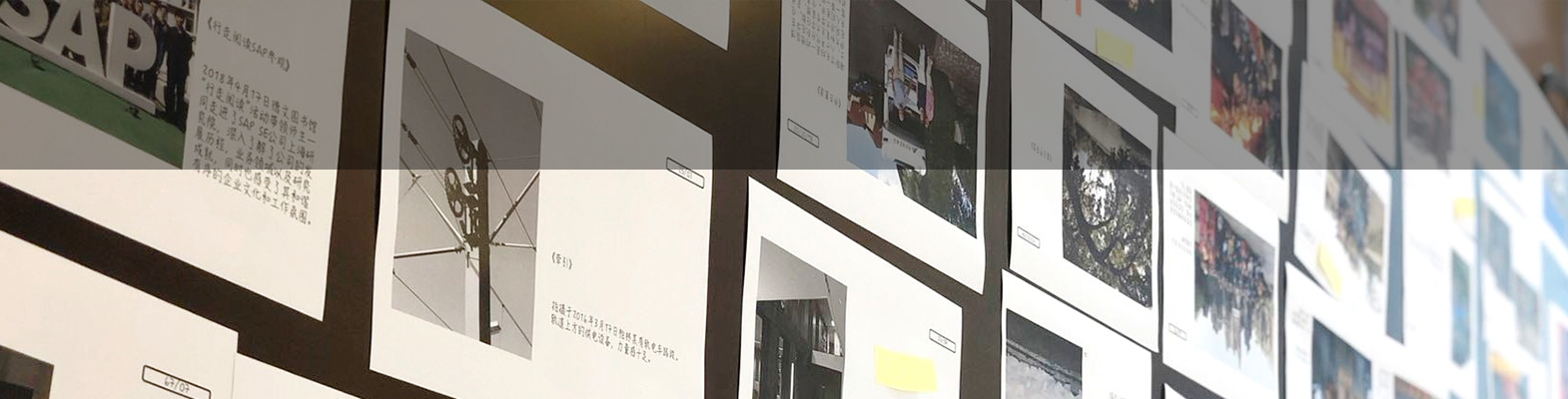赘言
作为日耳曼学者,一直以来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太多太多德语的重要著作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为了稍微弥补一下这个缺憾,也算略微尽一点德语学者的义务,我决定今年利用自己的专栏,来做一个“德语文化经典名著”的“尝鲜版”,从那些尚未被译成中文的德语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中,节选出一些段落,首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的中文读者。虽然天生鲁钝,但坚信凭借着认真的翻译,可以让国内更聪明的读者与更天才的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他们因为语言限制而无法领略的美好。另外,一人计短,在此也向广大的读者征询意见,问问大家,希望看到哪本德文经典文史哲著作的章节,我必定设法将它翻译出来。谢谢!
梁锡江
2018年4月于上海
《维吉尔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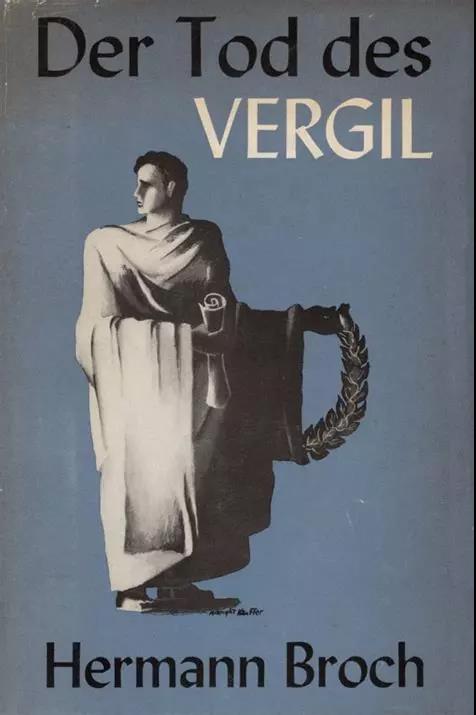
今天介绍的是我本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奥地利犹太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他1886年11月1日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一个纺织工厂主,他本来对于哲学和文学很感兴趣,但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入纺织学院学习纺织技术,期间曾经入伍。1908年子承父业,后企业倒闭。1928年,在他四十岁的时候,终于摆脱了世俗的牵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些数学、哲学和心理学。1930年代起专事文学创作,创作了长篇三部曲《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其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在德语文学中率先使用了独白与视角变换等表现手法,获得了较大的影响。1938年被迫流亡美国,后因贫病在1951年5月30日逝世于美国的纽黑文。
布洛赫生前曾有机会被推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怎奈造化弄人,过早离世,所以一直声名不彰,但在西方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对其为人与作品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高度评价他的作品《梦游者》,认为是现代西方文学的不朽杰作。而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内蒂则在获奖词中谈及自己的文学引路人时,专门向布洛赫献上了崇高的敬意。
布洛赫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对于时代价值的崩溃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而他的深入思考就反映在了他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1945)之中,这是一本号称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媲美的现代德语文学杰作,讲述了古罗马诗人临终前18个小时对自己一生及创作的反思。整部小说几乎没有情节,布洛赫大胆地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自始至终表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那无边无尽的内心独白。其基本情节大致是:身患重病的诗人维吉尔跟随罗马皇帝屋大维由希腊返回意大利,在港口他被人用轿子抬进了皇帝的行宫。在漫长的黑夜里,维吉尔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认为自己给人类带来了鼓舞和力量,但同时又对人类的精神起了麻醉的作用。他创作的作品脱离了现实,那种美完全没有意义。于是他决定销毁史诗《埃涅阿斯纪》的手稿。第二天清晨,两个朋友来看望他,他们就当代文学展开了争论,维吉尔要求他们帮助他烧毁作品,但遭到拒绝。后因为皇帝指责他出于嫉妒不愿献出作品,他只能交出手稿,委托朋友予以出版。最后,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目睹了整个地球的创生,具有浓重的迷幻色彩。小说通过诗人对于自己作品价值的怀疑,提出了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问题。
《维吉尔之死》
水——抵达
湛蓝而又轻柔,那是亚得里亚海(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波浪。迎面拂来的微风细弱得让人无法觉察。它吹动着波浪涌向罗马皇帝的舰队。舰队正驶向布林迪西姆港(布林迪西姆港(Brundisium),古罗马的港口城市,即今天意大利东南部的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滨临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已经可以望见卡拉布里亚(卡拉布里亚(Calabria),意大利最南端的地区,即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凸起,卡拉布里亚山脉贯穿全境。)海岸上平缓的山丘正逐渐逼近船的左侧。此时此刻,海洋那明媚、但却预示着死亡的孤独转化为人类活动的祥和欢乐;此时此刻,海潮上流溢着温柔的灯光,暗示着人类栖居之所的临近,潮水之上是熙熙攘攘的船只,有的和皇帝的舰队一样正驶向港口,有的正从港口中驶出;此时此刻,沿着被海水冲刷得洁白的海岸,在许多村子修筑的小型防护堤那里,竖着褐色船帆的渔船已经离去,为的是夜晚的捕捞。就在此刻,海水变得如镜面般平滑。在海的那一头,天空像是打开的贝壳,焕发着珍珠般的光泽,已经是傍晚了,人们已然闻到炉灶里炭火的味道,生活的声响此起彼伏,一下敲击,或是一声呼唤,都被风从那边传了过来。
七艘高船大舰首尾相连,正以先进的纵列方式行进。里面只有首尾两艘狭长的、装有船艏撞角的五排桨舰属于战舰队;其余的五艘船速较慢,但看起来更加气派,分别是十排桨和十二排桨的类型,建筑样式雍容华贵,与奥古斯都的宫廷风格完全相称。中间的那艘最为豪华气派,那青铜打造的船首金碧辉煌,船舷栏杆下面,饰有圆环的狮子头像金光闪闪,侧支索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三角小旗,在紫色的船帆下,耸立着罗马皇帝庄严气派的帐篷。而在尾随其后的那艘船上,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就躺在那里,死亡的征兆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额头。
饱受晕船之苦的诗人绷紧了神经,因为病症随时都会发作,所以他一整天都不敢挪动身体,不过,在船只到达较为平静的海岸区域后,一种松弛感忽然潮水般席卷着他,尽管他被困在了为他搭建的卧榻上,他却终于感觉到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生活,那是多年前就已脱离他管辖的藩属,如今却仿佛成了某种之于松弛感的独特回忆,重新探索着,重新体味着。海风劲吹,益于身心,那潮起的倦怠感能给人以沉静的抚慰,也许本可以转化为彻底的喜乐幸福,然而那扰人的咳嗽却适时出现了,每晚的高烧,每夜的恐惧,人早已憔悴。他,就那样躺在那里,他,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他,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他,就躺在那里,衰减的意识,几乎因为自己的无助而羞愧,几乎因为如此的命运而恼怒,他呆呆地望着焕发着珍珠光泽的天穹:究竟为何他会屈从于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指古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屋大维。)的催逼?究竟为何他要离开雅典?
荷马那神圣晴朗的天空本来会有利于《埃涅阿斯纪》的完成,如今这希望已然破灭;他也曾期望在柏拉图的城市里过上一种哲学与科学的生活,远离艺术,远离诗,期待那本将开始的不可估量的全新生活,如今每一个希望都已破灭;他也曾期望可以再次踏上爱奥尼亚(爱奥尼亚(Ionien),古希腊时期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古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尔那索斯以北,此外还包括希奥岛和萨摩斯岛。一些重要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均在此形成。)的土地,如今这希望也已然破灭;噢,破灭的还有那认识的奇迹以及在奇迹中得到救赎的希望。为何他放弃了这一切?自愿的?不!它就如同是那些不容抗拒的生活的强力(Lebensgewalten)的一个命令,那些不容抗拒的命运的力量,尽管有时这些力量会潜入地下、潜入不可见、不可倾听之处,但是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反而顽强地作为那些强大力量(Mächte)玄妙莫测的威胁出现,这些强力人们根本无从摆脱,在它们面前,人们必须总是表示臣服;它就是命运。之前他听从于命运的摆布,如今命运把他推向了尽头。这不一直就是他生活的形式吗?他曾经有过别样的生活吗?
天空那焕发着珍珠般光彩的贝壳,春波荡漾的海洋,群山的歌唱,他胸中痛苦的歌唱,神的笛声(长笛乃是牧神潘使用的标志性乐器,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曾言道:“当我们起舞、歌唱和饮食时,没有任何东西像长笛的乐声那样美妙。”),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事件,这事件就如同天穹的容器,很快就要将他吸纳入内,以便送他进入无限之中,对他来说,这一切可曾有过别样的意义?他生在农家,是一个热爱尘世和平的人,一个本该适合于在乡党间过着简朴稳定的生活的人,一个根据出身似乎已经注定可以且必须留在那里的人,然而一个更高的命运虽没有将他与故乡分开,但却不让他在故乡继续留下;它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乡党,赶进了茫茫人海间最赤裸、最恶毒、最狂乱的孤独之中,它把他从原初的简单中驱逐,驱入了日渐巨大的繁复与广阔中,如果有什么东西由此变得愈加巨大或愈加宽阔的话,那只能是他与本真生活的距离,因为确实如此,只有这距离增大了:他只是在自己田地的边缘漫步,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他成了一个动荡难安的人,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劳作,逃避着劳作,一个爱人者,同时却又是一个劳碌者,一个在内外激情的操纵下犯错的人,一个自己生活的过客。
而今天,几乎已到了自己气力的尽头,在自己逃亡的尽头,在自己找寻的尽头,他终于痛下决心,准备告别,痛下决心是为了有所准备,准备接受最后的孤独,准备踏上通向它的内在归途,但就在此时,命运和它的那些力量再一次控制了他,再一次阻止他亲近简单、原初和内在,再一次把他的归途引向别处,引向通往繁复的外在之路,把他重新逼向那遮蔽了他一生的恶(Übel),似乎命运只还留给他唯一一件简单的事情——死亡的简单。
专栏作者
梁锡江,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语言学史,德国科技史,德国浪漫主义,奥地利20世纪文学。主要译作有《道德的谱系》、《缓慢的归乡》、《骂观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