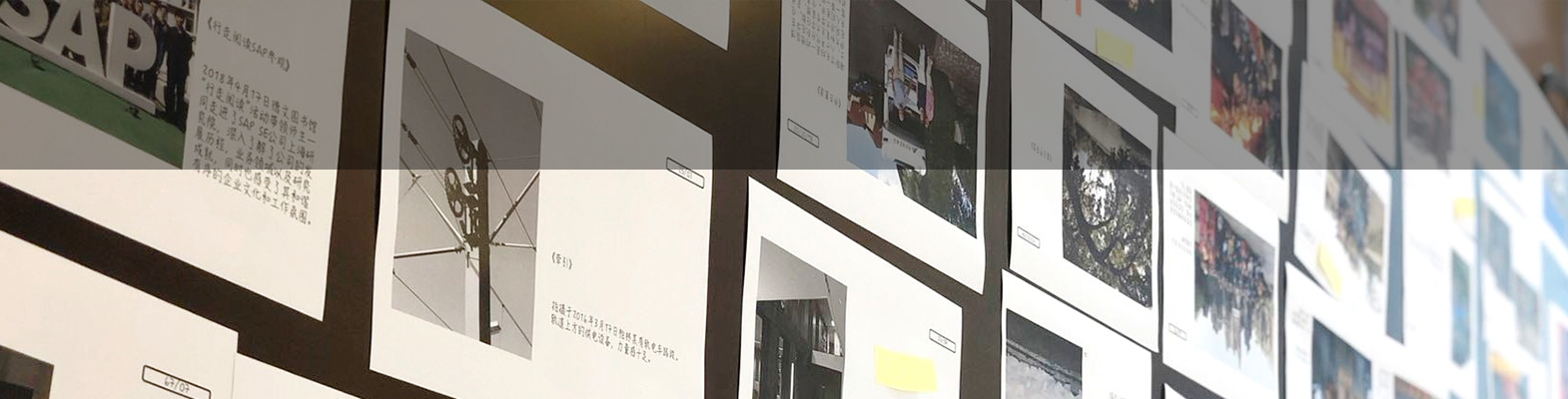编者按:据闻欧洲学界有个说法,完成康德著作英译本需历时百年。面对李秋零教授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300万字的文稿,我们在想,对于一个有着多领域研究和教学任务的人,到底怎样完成这样宏大的工程?每天工作15个小时?持续工作10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能够紧紧抓住当下的精彩,就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倘若,全是如此,或许人类历史就要平淡许多。幸而,有人有勇气走上一条较少人走的路。就像李秋零教授,他选择了《康德著作全集》的编译。十年潜心于此,他得到了跨越时空与200多年前的哲人康德漫长对话的机会。他创造了一项堪称不朽的事业。
1999年9月,人民大会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颁奖典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把“工具书、译著、学术资料类”一等奖证书颁给8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苗力田先生,握手祝贺由苗力田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10卷本出版。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希腊,赠送给希腊国家元首的是苗力田先生主持编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说过:“在哲学之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必得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
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成的说法更为人熟知:“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二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
康德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其逝世后的200多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哲学也从康德的古典主义发展到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
如果列举三位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康德显然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立三甲。在西方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事实上是两个支柱,康德之于哲学,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卢梭之于政治学。为此,康德哲学理所当然的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而理解、研究其思想,其前提就是语言的转换,即翻译。翻译既是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研究的延伸。
1999年,年过八旬的苗力田先生在完成《亚里士多德全集》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雄心勃勃地组织队伍,启动《康德著作全集》编译,并提议李秋零任主编。“翻译《康德著作全集》是中国几代哲学工作者的宿愿。再等待下去就是对民族的犯罪。”苗力田先生动情地说,康德著作的全新翻译必要而急迫。
中国人翻译康德的著作迄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历史,成就值得肯定,但也逐渐暴露出为学界所诟病的弱点。如语言方面,康德原著绝大多数是用德语写作,而我国较早的重要译者,均从英译本转译,使准确度打折;译者自身语言,尤其明显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译作,语言半文半白,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译作本身,误译漏译、专业术语混乱,风格不统一等等。此外,译著多集中于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相关著作,其中《实践理性批判》已达7个版本之多,而其他著作则翻译较少。这就使得对康德的完整理解仍有待完善。
然而仅半年光景,苗力田先生逝世,译事全部落在他的学生李秋零肩上。
李秋零曾在德国留学多年,对德语、拉丁语和德国哲学都相当熟稔,上个世纪80年代曾参与《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工作。师从苗力田先生,“确切、简洁、精通可读”的编译准则影响了李秋零。在《康德著作全集》中,首次解决了时人对于康德原著引用和理解不完整的缺憾,其全部的翻译都基于原文的语言,即从原汁原味的德文或拉丁文原文翻译成中文,并相对统一了康德哲学术语的译名,对一些重要术语提出了新的译法。随着《康德著作全集》(中译九卷本)的面世,汉语学界终于将拥有康德著作的全部翻译。

“我把学术当事业”
《康德著作全集》(中译九卷本)共约340万字。其中除了康德早期的几篇小文为他人译、李秋零校,《道德形而上学》为李秋零、张荣合译之外,其余全部为李秋零教授独自完成。正如《康德著作全集》责任编辑李艳辉评价的一样,“在当今学界,能下这等苦功夫做事的人着实不多了。”
“我不仅仅把学术当作职业,而是当作事业在做”,李秋零教授这样评价自己对学术的执着。他说,在大学期间,对学术的这种执着已确立,在此后的人生路程中,这种信念也并非毫无动摇过。他曾经有多次从政或者经商的良机,虽然自信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出于对学术的挚爱,斟酌再三还是放弃了,“学术是我的人生积累,尽弃前学实在于心不忍”。
十年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一次长跑。十年中,为了潜心于翻译,李秋零的办公室门口贴着“非约勿扰”的纸条,手机也经常处于关机状态;电子邮箱却被设置为5分钟收一次邮件,因为除了上课和出差,以及必要的外出,他每天都在电脑前端坐。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已是常规,全部家务也交由妻子处理。回忆于此,他说:“《康德著作全集》完成了,于我是一种喜悦,另一方面,对于因工作被疏忽的女儿,内心也有一种愧疚”。
“路得自己走”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是抽象思辨和具体感官享受的结合体”,编译《康德著作全集》的十个春秋,在别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于李秋零教授,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生状态。因为抱着“下定决心走这条路,就要把这条路走好”的坚持,学术早已成了他的人生状态。
从青少年时代的两次辍学,到成为当时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从八年的农村劳动,到跻身当代哲学研究的前列;从无片纸可读,到精通拉丁文、德文,著作等身,在李秋零教授身上,凝集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烙印,更激荡着时代人物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李秋零生于1957年,“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他经历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遭遇,而且由于家庭成分问题,从小就要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然而,精神上的折磨也许恰恰成为思考的起因,激起了他朦胧的反思,促成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最初领悟。当时对社会、人性、公平等等问题的追问,今天看来都是引领他走上哲学道路的朴素思考。“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哲学,思考的问题却是哲学式的。”李秋零这样描述自己哲学之路的缘起。
谈起个人的成长与那个时代,李秋零说“道路要自己琢磨”。“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复杂多变,你不知道社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生活面前,有太多的未知数。社会只提供条件,路还得自己走。”他认为,那时的挫折和失败,一定程度上促使那一代人更多地独立思考,更能冷静面对失败和挫折。他说,“那一代人的执着与坚韧,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
这种“路得自己走”的主张,始终贯穿在他的学术与教学的生涯。他回忆说,1983年去德国留学,第一件痛苦的事就是选课。当时国内的大学,几乎无选修课,而在德国,要从100多门课中完全自主选择自己的课程。“从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感受到的甜头”,他说,你可以“自己塑造自己”。
为此,在学生的培养上,除了因材施教,他还鼓励学生自主选题,“更多的是自己做”。他说:“我做的是否定式的工作,更多告诉你哪些不能做,但究竟怎样做,要学生自己去领悟”。他认为养成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的习惯,更利于学生长远的发展。
“而今始逢不尽泉”
“少时空有畅饮志,而今始逢不尽泉”,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李秋零教授写下的这两句诗,道尽了彼时的心情。学术殿堂广阔的天地与深邃的涵养激发了他献身我国哲学事业的远大理想。
1987年至1991年,李秋零师从苗力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苗力田先生在新中国最早开讲外国哲学史课程,在我国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是名符其实的拓荒者。他以羸弱之身躯奋斗了84个春秋,经常是病榻上授徒,晚年还热心《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工作,可谓“一代宗师”之典范。
在李秋零教授的学术道路上,包括研究康德和编译《康德著作全集》,都与苗力田先生有着直接的渊源。
谈起苗力田先生,李秋零说,学术上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严谨的学风,对原文原著的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苗老师在人格上的淡薄名利,待人以善,甘愿坐冷板凳,这些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他认为,“苗门弟子”团结友好的氛围,与苗先生“做学问先做人”的一贯主张密切相关。“和苗老师之间犹如父子的亲情感受,不仅是我,苗门其他弟子也有如此的感受”,“他对学生很严格,又很关心,那种关心是长久的,甚至到你工作了亦如此”。当年,苗力田先生曾怕李秋零喝酒耽误工作,以至在他酒后跟踪观察。如今,李秋零教授每次吃饭,也会记得哪个学生喜欢什么口味,还会照顾性格拘谨的学生,以至每次和这些学生聊天都会叫上相熟的人。
当年,苗力田先生七旬高龄披坚执锐,率领初出茅庐的弟子,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如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无穷尽也”。
资料来源: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网,2010年4月28日
https://www.sinoss.net/2010/0428/20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