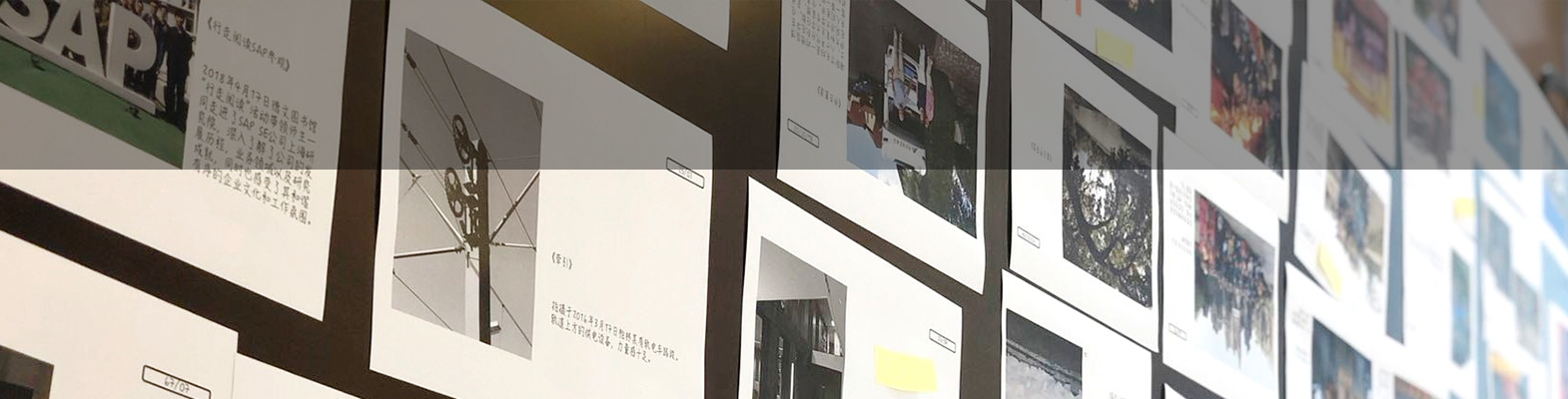作为日耳曼学者,一直以来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太多太多德语的重要著作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为了稍微弥补一下这个缺憾,也算略微尽一点德语学者的义务,我决定今年利用自己的专栏,来做一个“德语文化经典名著”的“尝鲜版”,从那些尚未被译成中文的德语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中,节选出一些段落,首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的中文读者。虽然天生鲁钝,但坚信凭借着认真的翻译,可以让国内更聪明的读者与更天才的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他们因为语言限制而无法领略的美好。另外,一人计短,在此也向广大的读者征询意见,问问大家,希望看到哪本德文经典文史哲著作的章节,我必定设法将它翻译出来。谢谢!
梁锡江
2018年4月于上海
在德国,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思想在知识界具有显赫的地位,被誉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列举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四种主要哲学思潮,即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卢卡奇、布洛赫、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尽管在提到20世纪德国哲学的有影响的人物时,国外学者之间存在着各种看法,但他们往往都不会漏掉布洛赫的名字。他与青年时代的好友卢卡奇【他与布洛赫于一战前相识于布达佩斯,后同在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圈子里崭露头角。有意思的是,《乌托邦精神》一书的创作时间与卢卡奇的两本著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分别同时在一战前酝酿《乌托邦精神》(第一版)与《小说理论》,1923年《乌托邦精神》(第二版)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又同时出版。】等人一同开创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 kontextwochenzeitung.de
恩斯特·布洛赫在1918年出版了成名作《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对乌托邦问题的研究,并一直保持多产的状态,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他带来了崇高的声誉,而且还滋养了许多后来人。阿多诺在青年时代就经常阅读的两本书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马尔库塞在一次布洛赫也参加的学术会议上承认,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至少影响了一代人。而哈贝马斯也是在青年时代通过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乌托邦精神》才开始真正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兴趣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历史上,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乌托邦精神》封面 © amazon.de
下面是我翻译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缘起”,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布洛赫撰写此书的意图。
缘起(1918[1],1923)
我存在。我们存在。
这就已足够。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了。生活被给定到了我们的手中。就其自身而言,生活早已变得空洞。它步履蹒跚,毫无意义地徘徊,但我们却岿然挺立,因此我们意欲成为它的手段与目标。
曾经的存有,可能很快遭到遗忘。惟有某个空洞且可怖的记忆还搁浅在悬而未决的空气中。是谁得到了庇护?是那些腐败者,是那些卑鄙者,是那些盘剥者。新生者,则被迫坠落,被迫趋向死亡,为的却是成就那些陌生且仇视精神的目标,然则那些可鄙之徒却得到了拯救,高坐于温暖的房舍。他们中无人迷失,但那些曾挥舞着别样旗帜的人们,他们挥舞了那么多的鲜花,挥舞了那么多的梦想,挥舞了那么多精神的希望,如今却已死亡。画家保护了中间商,捂热了那些始作俑者的后庭。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目标,是有史以来最黑暗者;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为中庸者所施加,为中庸者所忍受;愚蠢大获全胜,宪兵队为之保驾,智识者为之欢呼,彼等知识分子搜肠刮肚,寻找颂扬的词句,只恨自己的脑汁不够。
然而,这一切至今依然存留,就仿佛大家觉得之前的创伤来得还是不够彻底。战争结束了,革命开始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放的大门。不过,没错,这些门不久又重新关闭了。门闩抬起,然后落下,一切老旧者又重新在彼处堆积。放高利贷的地主,有权有势的大资产阶级(Großbürger),他们将现实中的火苗逐段地熄灭,而遭到恐吓的小市民们(Kleinbürger)只能一如既往地继续煎熬出坚硬的外壳。那些非无产的青年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野蛮,更加愚蠢,大学成了精神的真正坟场,里面充斥着腐坏的臭气与顽固的黑暗。于是,那些表面的被修复者与被复辟者们集体让一切再度上演,正如一个世纪前[2]反动派们所演示过的那样:那是关于“乡土”的口号,所谓的爱国文化的传统主义;还有那个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只看到月光下魔法之夜的骑士古堡高高耸立,却把农民战争[3]彻底遗忘。普通的文人们也跟着再次变得保守,他们这些言辞表达的祭司们加紧工作,烧毁不久之前他们还在顶礼膜拜的东西,支持那些垦荒殖民事业上的废物,从过去那雅致的废墟中拼凑出赝品,阻断未来感觉、城市感觉和集体感觉的去路,使其无法从事生动的塑造与构型,将反动派的投机与欺骗置于更好的意识形态之中,让他们那蹩脚的卫生事业以及那来自二手模仿的浪漫主义变得绝对化。与此同时,西方数百万的无产者却还没有发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在俄罗斯不屈地挺立,而那些永恒的问题,它们属于我们的渴望,属于我们的宗教良知,它们还在继续燃烧,它们提出的那绝对的要求同样的不屈,但也同样没有得到兑现。此外:与一百年前一样,我们至少从对真实的观照中学到了东西;马克思将那种完全虚假的、抽象得毫无启发性的狂热,那种纯粹的雅各宾主义[4]从社会主义式的冷静考量中切割出去,而我们更加不会遗忘一切现实政治之上的康德[5]与巴德[6]精神。与之相反,新一代反动派的浪漫主义未曾继承任何合理的东西,它既不现实,也不动人,更不具备普遍的精神意义,而只是单纯的愚昧、狭隘、无知、非基督教化。他们从所谓的“乡土羁绊”(Bodenständigkeit)的激情中最终只能诱引出西方的没落[7],那是纯粹的奴才式的狭隘,那是非宗教性的幻灭:干枯的蓓蕾,飘零的花朵,对于今日而言,只有文明的凋谢,海洋事业与历史档案室里的悲观主义,成了唯一的目标,而对于整个欧洲而言,却是即将到来的永恒死亡。
虽然事情已必然如此,但它最终也可以与我们相关。我吃谁的面包,就应该唱谁的歌。但正是这场围绕金牛犊以及牛皮鼓的舞蹈[8],而不是其背后的其他东西,是令人吃惊的。这也造成,我们没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变得比那些热血动物还要贫乏可怜;主宰一个人的神明,如果不是肚皮,那么就是国家,而其余的所有都沦落为消遣和娱乐。我们有渴望,有短浅的知识,但却少有行动,而且——这也同时解释了行动匮乏的原因——还缺乏广度,没有前景,没有结局,没有内在的、预期中可以被超越的界限,没有内核,缺少集聚性的总体的良知。而在这里,在这本书里,恰恰沉淀着某种开始,那从未逝去的遗产重新找到了自己;因为那最内在者在这里重新照亮了彼处,所以它并非某种卑劣的似是而非,不是某种空洞的上层建筑,而是摆脱了所有的面具与过时文化的那个“太一”[9],那个被不断找寻的东西,那是一种预感,一种良知,一种拯救;它从我们依然完整的内心里,从我们白日梦[10]的最深处与最真实处脱颖而出:这白日梦既是我们依然存留的最后的东西,也是唯一值得存留下去的东西。此书中,你将被引向我们的人物形象与萌芽中的收藏品;书发出了声音,通过某个单纯的古瓮,来说明一切“造型”艺术那先验隐藏的主题,以及音乐所有魔力的中心,最终还通过与自我的最不可能的遭遇,通过生命瞬间的意识黑暗[11],来说明其是如何突然出现的,又是如何在那个无法被构建的绝对问题上,即那个自在自为的“我们的问题”上聆听自己的。这一内在的道路,又被称为自我遭遇,首先将通向如此的深处,它是内在言语的调配,如果没有它,所有投向外界的目光将毫无意义,也就不会有任何磁力、任何力量来吸引内在的言语来到外部,并且帮助它突破世界的错误。当然,在最后,在探讨了内部的纵深问题之后,广度的问题,即灵魂的世界,那是乌托邦的外部的宇宙功能,将得到展开,用来对抗苦难、死亡与物理的表层世界。只有我们内心里,还亮着那道光,而朝向它的梦幻之旅已经开始,我们要对白日梦做出解释,并且掌握这一乌托邦的原则性概念。为了发现这一概念,发现合理,以便能够体面地生活,并且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富有时间,于是,我们走上了、开辟出那些形而上的本质道路,呼唤那尚未存在者,将其镶嵌于自由的天空,将我们自己镶嵌于自由的天空,并在现实消失的地方寻找真实者、真正者——incipit vita nova[12]。
[1] [译案]《乌托邦精神》初版于一战中,即1918年,布洛赫后在1923年对该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使其内容更为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而此篇“缘起”在两个版本皆有收录,但文字不尽相同。
[2] [译案] 指王朝复辟时期。即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830年与1848年欧洲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旧王朝及欧洲封建秩序得以恢复,反动派们指的是当时的欧洲旧势力。
[3] [译案] 指爆发于1524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当时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民因为不堪重负,奋起反抗争取自己的权益。其著名的领袖有布洛赫推崇的闵采尔等,该起义后来被德国封建主镇压。此处意指德国浪漫派只知道推崇中世纪时期的骑士文化,却遗忘了当时还发生了农民战争这样的群体事件。
[4] [译案]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所推行的恐怖统治政策。
[5] [译案] 当是指康德的伦理、国家以及永久和平的思想,详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何兆武译。
[6] [译案] 指弗兰茨·克萨韦尔·封·巴德(Franz Xaver von Baader,1765-1841),德国哲学家与天主教神学家,对谢林的影响很大。与谢林一样,反对片面的理性主义,主张对人类理性的自我限制。主张信仰主义,认为哲学必须建立在宗教学说之上。
[7] [译案] 影射施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该书共两卷,出版于1918-1922年间。
[8] [译案] 金牛犊是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的一尊偶像。根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2章记载,金牛犊是亚伦制造,以取悦以色列人。在德语中,“围绕金牛犊舞蹈”也有“拜金”的含义。
[9] [译案] 太一(das Eine),按照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的说法,世界万物都是由“太一”产生出来的。“太一”是绝对超然的神,是一切存在物的源泉和最终原则。它绝对超出一切思想和存在之上,不能用任何物质的或思想的属性来说明它。
[10] [译案] 白日梦(Wachtraum):在布洛赫哲学中,“梦”乃是进行预先推断的意识所拥有的核心表达形式。夜梦与白日梦均构建意欲的图景,这些图景能够超越有缺憾的现实,同时包含了某种更好生活的投射,这些投射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在布洛赫看来,尤其是白日梦具有高度的社会乌托邦潜质。
[11] [译案] 生命瞬间的意识黑暗(Dunkeldes gelebten Augenblicks),乃是布洛赫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原初动力,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即“熟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精神现象学》序言),即在我们所在的那个瞬间,其实我们认识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当这个瞬间成为过去,抑或当这瞬间还处于被期待的前状态时,我们才能对这一瞬间有所了解。这是一种直接的黑暗,它贯穿于整个世界,它的时间形式就是现在,它的空间形式就是这里。而这种直接性也需要中介,即通过其自身来得以被阐明。请参见下一章节《自我遭遇》中的“太近了”部分。
[12] [译案] 拉丁文,新生活开始了。
专栏作者
梁锡江,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语言学史,德国科技史,德国浪漫主义,奥地利20世纪文学。主要译作有《道德的谱系》、《缓慢的归乡》、《骂观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