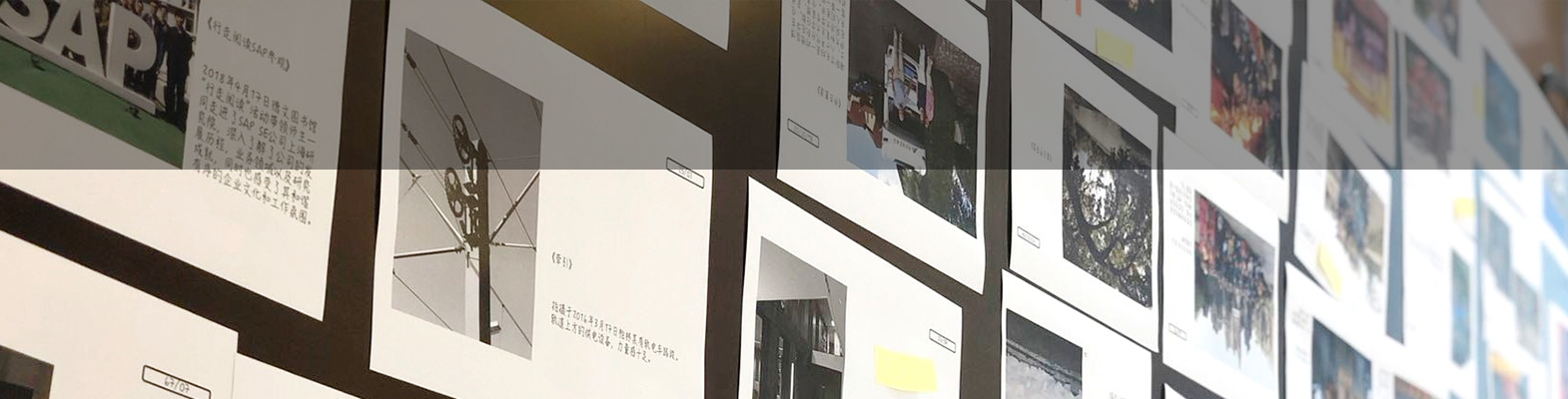我当然是一朵玫瑰! 两个农民,同甘共苦,一份爱情,几多闲适。丽江,一个慢生活的所在。
“我当然是一朵玫瑰!”
和洁华与和桂月,一对纳西农家夫妇。
要想幸福一时,就喝个醉。
要想幸福三天,就结个婚。
要想幸福八天,杀猪请客。
要想幸福一生,造个园子。
——中国智慧
前面几天,我们都在大城市里转。城市寄托着中国人逃离农村苦日子的希望,这里水泥建筑绵延不绝,一直蔓延到郊区,无精打采地等待着幸福的降临。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商业区,却也藏着许多悲伤。在这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好像一片匆匆掠过现代社会的小小的灰色倒影。很多访谈对象都说自己想去隐居,他们渴望静修,渴望在大自然的宁静中畅快呼吸、寻觅灵感。之前我无非是好奇地倾听,但现在我有了亲身体会。我也感到不快乐,想远离永不停歇的大都市,它像磨盘,又像烈焰,仿佛随时随地都能让人粉身碎骨。
于是我们来到中国西南部的丽江。它简直就像一个启示。我们降落在一个小小的机场。阳光,晴空,大山。机场外面等候旅客的人中间,有人带着一条大狗。大城市里只能看到小狗,迷你型的小狗——城里的狗狗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尽可能地压缩自己的生活空间,避免打扰他人。这里可是只大狗,喘着粗气,自由自在,充满活力。

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风景从窗外掠过,这里是纯粹的山野。我看到一个钓鱼的人,一个真正的垂钓者,宛如一张中国风景明信片。幸福来了!我兴奋莫名,活力回归,阴霾不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里总是有一股蔬菜的味道。这气味算不上特别宜人,不过这会儿的我闻着菜味儿也一样高兴。但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呢?车窗外明明只有荒草丛生的田野。
我的导游兼翻译王波已经和司机说上话了。要把我的那些问题解释清楚,还是得费点口舌的。每次他都不知道要说多少话!每当司机终于恍然大悟,两个人就会笑起来,随后又讲一大堆话,王波时不时长长地哦一声,点头表示明白,又接着问这问那。这样的过程总是重复,每次都一模一样!而我自然是永远迷惑,只能急切地问他说了什么,妄想插进高速进行的对话里去,心里满满地期待着从长篇大论里衍生出的精彩人生。但王波会转过头来简短地说:半杯水。然后又掉头不顾了。我把他拉回来:半杯水?就这?他点点头。可是他说了许多话啊?王波耸耸肩。没啥重要的。我只能叹口气。不过,也有些时候,王波下车的时候会心满意足地说:很有意思,他讲了很多故事。这回的“许多话”终于有内容了。
王波如今可谓业务熟练,不待我提醒,他就会主动去跟出租车司机搭话。他总是在车里一坐定就马上开展攻势,去赢得司机的信任。这回的出租车载着我们穿行在美丽的绿色山野中,气氛友好而随意,和司机的聊天渐渐变成讲故事,内容越来越有意思。司机的手臂上缠着好多珠串,操纵杆上套着毛线织的红白花套子。司机告诉我们自己是纳西族,这个少数民族是是西藏牧民的后裔,10世纪的时候迁居来此。他用自己的车跑出租才4年,有时也带带旅游团。他的儿子在昆明学体育,花费很大,所以他开出租挣点外快。

挣外快?我一下子来了兴趣:那他本来是做什么的?于是他们两个又说了很多话,王波断断续续翻译道:“他是个农民。”“有田,搞有机农业。”“种水稻和玉米。养鸡、养猪,还有……” “哦,农民”,我回答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然后我也看到了——座椅背后放着一大堆蔬菜。我刚才怎么就没注意到呢?王波,我扯了扯他的袖子。赶紧问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上他家看看。”王波问了,这回只有短短几句,司机随便点了点头,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可以去。王波在前座上欠了欠身,把包拿在手里,我知道我们马上到地方了,可又忽然想起专为出租车司机准备的第二个问题。“王波,问他花,你有没有问他想做哪种花?王波点点头打开车门。他说什么花都行,他说,都行!好吧,我说。能有这样的回答也不错了。
关于花儿的问题令不少出租车司机感到尴尬。也许这个问题太过个人,或是有些女性化,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很多人觉得自己开出租这个职业不够高端,非要选一种花的话,他们会选择尽量低调的、不那么香的花。和洁华就没那么自谦了,不过他也不能算真的出租车司机,他是农民。把自己比做一朵花并不让他感到为难,但他也不会由此发什么思古之幽情。花就是花,仅此而已。
第二天,他如约来接我们。我们先走了一段和昨天从机场出发同样的路,不过是反方向,然后转弯下了高速。半路上,和洁华在田野里把车停下,高高的作物中间有一个妇人正在劳作。她停下了手头的农活,摘下草帽,上车后座和我们坐在一起。她就是和洁华的妻子和桂月。她友好但矜持,一声不吭,就这么静静地坐到家。车子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他们两口子的家在一片很大的农田中间一个很小的村子里。

哇!我们一下车就忍不住惊呼,我们心里还怀着从城里带来的郁闷和渴望。哇!”好一片田园风光。我们走进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猪圈、几棵石榴树、堆成小山的玉米、有些隐蔽的厕所,和宽大的木制门廊。我们东瞧西瞧。这里家家户户都用太阳能。洁华一边说,一边从垂在猪圈上方的枝条上摘下几个石榴。大白猪哼哼唧唧。它还不知道自己活不过两个月了,12月里杀年猪是村里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每到年底,村里51户人家轮流请客,酒席就摆在院子里,一摆好几个礼拜,从早喝到晚。洁华告诉我们,杀年猪的酒宴不可以缺席。婚丧嫁娶倒是不一定要去的。

我们走进客厅。桂月端来刚烤好的玉米。我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吃吃地笑着说,并无一丝感伤。从她的话里我们感受到的既有时间的流逝,也有两人的相守。她丈夫点点头,他还是以她为傲。他们的婚姻不是包办的,他在村里一次放电影的时候认识并爱上了她。婚后他们生活平等,一起务农,同甘共苦,互相依靠。他们都只上过小学,然后就要在家里帮忙干活,就这么送走了青春。没关系,桂月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但当我向她提出花的问题时,她却说:我当然想做一朵玫瑰花! 一朵和她年轻时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洁华给我看她手机里存的结婚照。哇哦!我惊叹。他俩都挥挥手笑起来。

我问他们,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最让他们感到幸福的东西是什么。洁华耸耸肩,我们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也许还是有的……没错,十字绣。桂月拿出她最大的一幅作品,摊开来。这是一条长长的毯子,绣的是红楼十二钗。我干了整整一年,她说。光是框架就花了一千元。 所以这幅作品价值不菲。当地许多妇女都喜欢绣花,桂月也一样。她说:趁我还做得动,就做些事。 这种话像是老人说的,可她其实才40岁呢。我们给她和十字绣拍照,客厅里有点暗。我们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大海。没,洁华答道,没时间去。山里的人都想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但村里的人都没有出过远门。有钱就盖房子,这是一生的事业。对于洁华来说也是如此。

刚搬来的时候,他说,房子是空的。 他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家打造起来。他们挣的钱除去家用,都花在父亲身上,洁华要承担父亲吃饭和看病的花销。他弟弟负责照顾母亲。姐姐应该已经出嫁了,照顾父母是儿子的责任。人生就是这么安排得明明白白,幸福也一样。我的幸福就是吃喝不愁,洁华说,就这样。 白天他俩为了糊口干活,就像俗话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晚上呢?我问。我们一般就呆在家里,洁华回答说,桂月绣花,我看电视,抽水烟。 桂月笑了。

我们出门闲逛。洁华指给我们看了他的家业和田地,又领我们到处走走看看。国家分给他一块地,无偿的,地里的收获全归他们自己。这里的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维持自给自足的健康生活。他们唯一的日常开支是每月30元的水电费和管理费,只此而已。种地全为自己,没有租金,不纳税费。我们听得万分惊奇,这简直是天堂了。但光靠这个还是不够生活的。 不过,这是一种鼓励政策,洁华解释道,为了把人留在土地上。就这样,洁华和桂月留在了农村里,住在一个和平静谧而又不无艰难的地方。只有附近机场起降的飞机不时从空中掠过,才会使人想起外面的世界。在德国,像这样不时从低空掠过的飞机往往引起居民抱怨。但洁华和桂月不一样,飞机让他们感到自豪。当我问到他们有没有特别幸福的经历时,他们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并指着天空给我们看头顶上的航路,它代表现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其实还是向往大城市的?不,不是这样的,洁华摇摇头,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他说,只是这里太阳太猛,把我们都晒黑了。但他又说,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
“丽江这地方挺无聊的”。
洁华说:那里的人九点去上班,十二点回家吃午饭,在家待到一点半又去上班,下午四点回家。 他笑着又说:我就没有这种压力。 他就这样站在我面前,站在村子的中央,站在绿色的田野中,悠然自得,无忧无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都相当满意。当然,这一切也并非真是那么完美,但当我问洁华,他看到周围的大自然的景色是什么感受,比如草地,远山......他会用美来形容这一切吗?我想到的是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但他说:没什么感觉,没啥特别的。

我们继续走。洁华在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他指着搭在一栋老房子构架上的一个小板棚。有个玩鹰人住在那里,他介绍说。他喊了一声,一个花白胡子、神色机敏的老人从充作房门的黄色帘子后面露出脸,看看有什么事。他认出是洁华,就笑着出来,踏进地基的红土里。这是他家房子的地基。他是一个准业主,他家房子正在盖着。宅基地有了,盖房子的钱也终于凑齐了,可以开始了。这里每人可以得到700平方米的土地。 他现在站的位置,很快就会建起他的第一栋自有房屋,所需费用相当于3万欧元。

玩鹰人已经78岁了,但现在开始盖房子还为时不晚。而且钱已经赚够了......等一下......老人绕过棚子,把手伸进里面一个更小的棚子里,回来时胳膊上挎着一只健壮的猎鹰。......看我的鹰!哈哈哈! 全城都认识玩鹰人,他整天带着鹰在丽江街头游荡,笑着收钱。游客付点钱就可以把他的鹰架在自己胳膊上。老伴和儿子恰好过来看这位精明的老人,我请一家三口在他们半完工的庄园里坐下拍个合影。

红土地上的安静生活令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是幸福的,玩鹰人说,笑得粗犷又深沉,从他脸上那深深的笑纹里看不到什么忧郁、深思和生活的艰辛。于是我把鹰架在胳膊上——我真的这样做了——我感觉到它的小心脏在兴奋地跳动,我很高兴它已经把钱赚够了。我们也向玩鹰人付了点钱,也许够他买一个门把手或者一口新锅吧。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刚才的拜访也只是顺路而已 ......一绕过灰色的围墙,玩鹰人就被我们抛在了脑后。生命如风而过,简单、短暂、微不足道,但即使在废墟和灰烬中,也总有那么些幸福,我想。当然,钱还是需要一点的。

于要多少钱才够,不妨去问问坐在瓦房顶上的许多陶土猫。与它们的近亲——一团和气的招财猫不同,这些陶土猫个个嘴张得比脸还大,显然是在渴望金钱。但在这里,居高临下盯着我们的不只是贪婪的陶土猫... 还有其他的生物挡在我们的路上。活物。因为现在正值十月,村子里到处都是巨大的蜘蛛。它们一堆堆地挤在灌木丛中,树上,墙头,到处都是,蜘蛛网铺天盖地。我们走的有些路简直就是蛛网隧道。我汗毛倒竖。一个蜘蛛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洁华注意到我的兴趣所在,随手拿起一只蜘蛛给我看,说这只黑黄相间的蜘蛛是无毒的。他玩着玩着,把蜘蛛丝从它的腺体里拉出来。我们拍了点照片,洁华开始想自己的事,也许不是。但有一件事他刚才肯定想过了,因为他忽然说:
“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语言了。我点点头,这话不错。花就是花。幸福就是幸福。而我,只要我愿意,我就是一朵玫瑰。
采访系列故事将在“”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问福中国】栏目连载,敬请期待。

Simone Harre(西蒙•哈尔)
作者简介:Simone Harre(西蒙·哈尔),德国人文学者,作家,为报刊撰写人物传记和文章,亦创作小说。她曾在德国和中国分别花费五年时间向人们询问对幸福的定义,并把她2014年以来在中国的访谈在德国结集出版。经她本人授权,“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对访谈集进行选译连载,译文视情况略有删改。本系列图片与视频均由作者提供。
https://simoneharre.com/
译者:俞宙明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