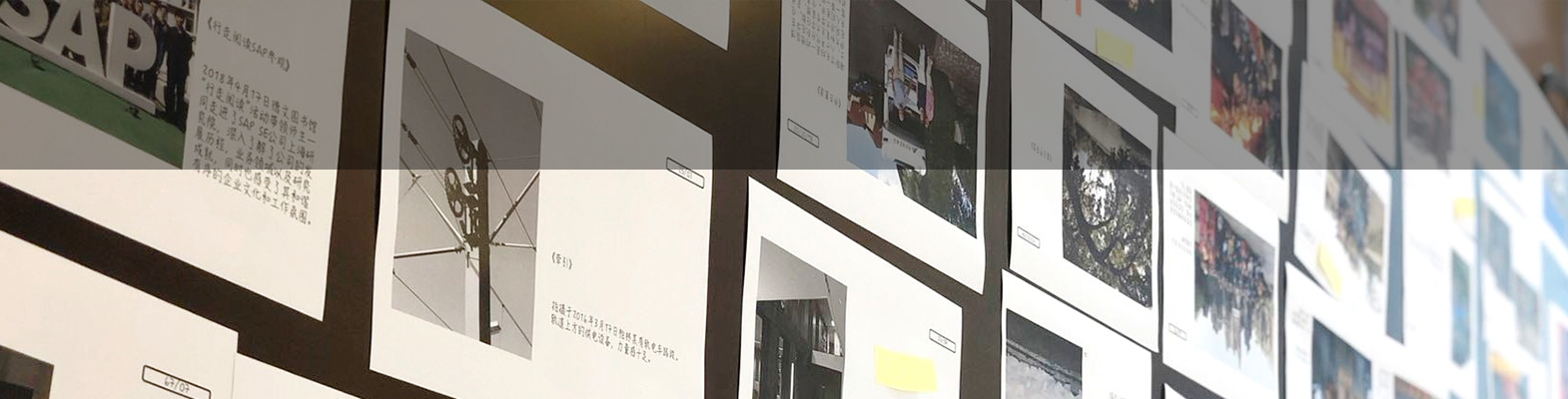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老德看中国”
司马涛(Dr. Thomas Zimmer),德国汉学家,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1980年代在北京留学,先后于德中两国各地高校开展汉学教学科研多年。2003年至今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研究重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希望能借此机会与中德两国的读者朋友分享关于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信息和思考。

余华 © ifeng.com
余华,中国作家,生于1960年。长期以来,他在德语图书市场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这尤其要感谢他作品的译者高立希(Ulrich Kautz)。在过去的十年里,余华的小说《兄弟》(中文:2008)上下册依次出版,其最新小说《第七天》(中文:2013)的德译版也于2017年出版。小说展现出余华对太平间氛围极其熟悉,这可以追溯到余华的幼年时期——余华出生于医学之家,最初就住在太平间对面医院的一片空地上。80年代初期,在余华完成学业并作为牙医工作几年后,他转向了文学。
德语读者们能从余华的文化批判反思作品《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文,2011)中想象当时中国的情况。余华早期文学作品对于德语读者来说,还有不少值得发掘的地方,他90年代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德译本已于2018年底面世。90年代也正是余华代表作《活着》(原1993)获得国际性认可的时期。该小说在1994年由导演张艺谋搬上荧屏,同年,影片在国际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在中国同时期的青年作家圈内,余华已享有盛誉。80后先锋派小说家如苏童、格非等,以其前卫、荒诞、扭曲的叙述风格吸引了读者。这一浪潮直到90年代初才渐趋消失,那一时期,余华等人开始在小说文学中探索新的潮流,又重新回到了传统叙述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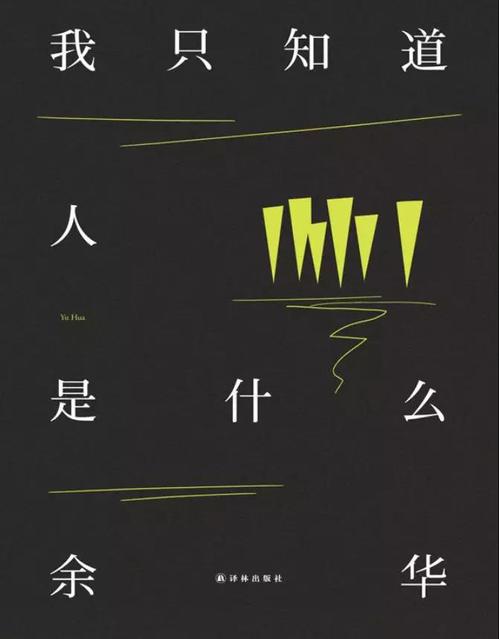
中国当代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并扬名于西方社会。人们能从作家的背景、文学发展、他们在中国文学论坛的地位以及对国家发展的判断了解到国家的情况,但这些都很模糊,因为有信服力的书籍来源和翻译家都很少。2018年出版的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则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补充——当然这首要是针对中国读者的。20多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接近20年(最早的文章写于1999年,而最新的文章写于2018年6月),文集收录了余华在各个国家的演讲稿以及他为不同语言的作品译本撰写的前言。
余华这本杂文集包罗万象。对于那些对文学发展和余华文学作品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他们能从文集中了解到余华各个作品的产生,以及余华追求个人风格的不懈努力。在讲述《活着》的某一场景构筑时,余华说:
“……当一个作家用朴素的语言写作时,比用花哨复杂的语言更困难,因为前者没有地方可以掩饰,后者随处可以掩饰。”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2017,武汉)
可以说,二十五年前《活着》出版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积极评价都在余华的预料之中。这部作品与余华文学风格发展有着紧密可见的联系,余华本人也评价道:
“继续说《活着》。这部小说发表好几年以后,我有时会想,当时怎么就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了,可能就是一条路走不通了,换另一条路。我曾经觉得这只是写作技巧的调整,后来意识到也是人生态度的调整。……《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2017,武汉)
余华还解释了他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
“……就像城市里的地标建筑一样,人们在寻找某一个位置时会把地标建筑当成方向来辨认,文学作品里有时候也应该有地标,这是时间的地标也是社会历史的地标,几百年以后人们回过头来,想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已经消失的某一阶段的社会历史时,需要这样的地标。”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2017,武汉)
这与余华的自信相符。当他把自己和作品放到过去和当代的传统严肃文学中看待时,他提及诗人欧阳修(1007-1072)和中国当代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
“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不是陪审团成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去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变得最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那是新闻干的活,而是在此后,欧阳修的诗句和鲁迅的文章就是此后的价值。”
(《我相信这就是人类的美德》,2017,武汉)
余华不是单纯在空讲,而是从他最了解的领域着手分析。与他反复提及的鲁迅一样,他认为文学创作是将时代弱点融入文学形象并赋予其历史意义的过程。余华所理解的文学是借用杰出的人物形象照亮历史维度,并且呈现历史的轨迹。余华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鲁迅《风波》里最重要的人物是赵七爷,不是七斤。当然七斤是小说叙述的角度,鲁迅是从七斤的角度来写的。这是反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势力反扑回来的一篇大变革时期的小说,仔细想想,其实我们都是赵七爷,我们在社会重大变迁的时期如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立在潮头的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赵七爷,都是审时度势把辫子盘到头顶上,又审时度势把辫子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这是面对社会巨变时的应对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式。”
(《我相信这就是人类的美德》,2017,武汉)
中国因其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没有宏大的叙事,相反,有的是很多小的、看似不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展现出余华总是力图运用简洁风格表达繁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一个很多事物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高尚的和粗俗的东西往往在同一个事物里。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进入宾馆的房间,看到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缸,边上竖一个牌子‘禁止吸烟’。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烟》,2016,纽约)
对于余华来说,文学也是一个合适的工具,能够把中国的复杂性介绍给全世界,并且不用害怕与外国媒体联系。基于余华与西方媒体的接触,他说:
“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跟欧洲的记者们好好谈谈西藏了,结果没有记者关心西藏,他们问的都是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在座的中国人里面有人听到我这么说可能会觉得西方社会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全世界的媒体都是这样,都热衷报道负面的,我们自己媒体对毒奶粉的报道比所有外国的报道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德国很重要的报纸《时代周报》,有点像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是那种八卦报纸,他们的总编辑告诉我,他们负面报道最多的是汉堡,因为这家报纸在汉堡,比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多几倍,而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又比对欧洲的多几倍,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又比对中国的多几倍。……我觉得负面报道多不是坏事,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充分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会引发人们的正义感,生气或者愤怒都是正义感的表现。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正能量,其实很多正能量是面对负能量时被激发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应该努力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发言题目待定》,北京,2018)
作者:司马涛(Prof. Dr. Thomas Zi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