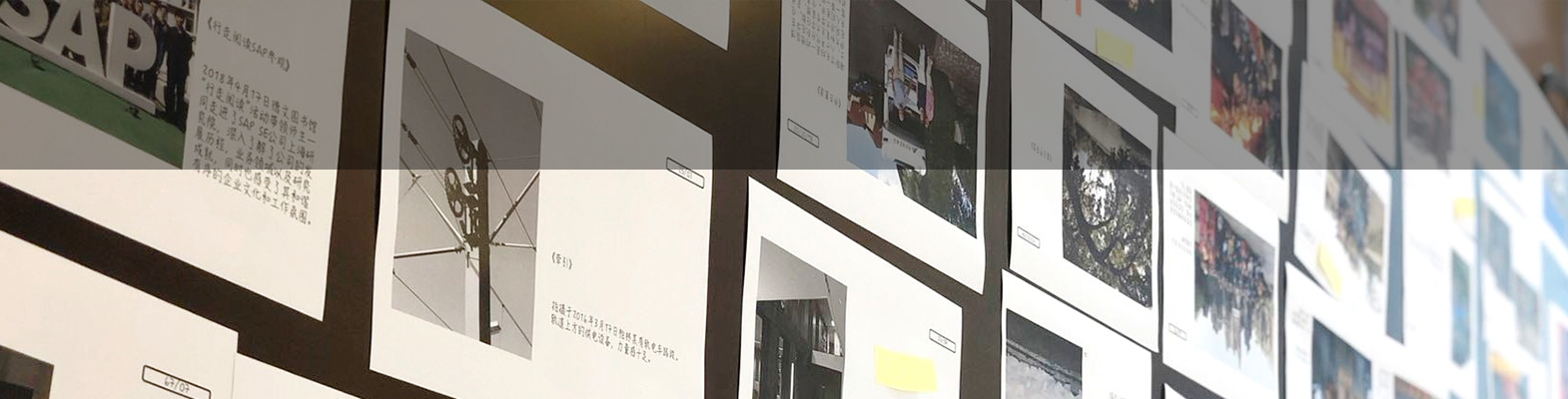专栏介绍
一中一德,相隔万里,日耳曼文化遇见中华文化。
两国双城,相向而行,在他乡遇见故乡。
“中德双城记”是发生在一座中国城市和(或)一座德国城市的故事。以一位“他乡客”视角开启双城之旅,当中德文化产生碰撞,奇妙的化学反应便产生了,这是一座你正在生活的“他乡”城市,而这里又让你遇见或回想起“故乡”,时日已过久居此地,究竟何处是他乡,何处是故乡?以城市之名,诉说中德交流轶事,感知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在碰撞与互动之中,不断迸发出一道道绚丽的火花。
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一路北上,我在回家的路上。
和女友安娜拥别后,这一次的意大利之旅就结束了,我搭上回程的巴士穿越欧洲的脊梁——阿尔卑斯山脉。巴士行驶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窗外的景色不留情面地飞驰离去。虽已是春风四月,经过奥地利狭长的土地,还是能看到被零星白雪覆盖的山脊。冰雪消融后留下的棕色土地,和皑皑白雪相互交映,像极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奶牛。我静静地看着窗外,娟秀细长的地中海柏树愈见稀少,取而代之的是枝繁叶茂的参天冷杉。

巴士经过雪山环绕的因斯布鲁克
看到漫山遍野的冷杉,我就知道,我离德国不远了。我看看手表,还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心里却突然莫名滋生一种特殊的情绪。一种期待与厌恶交织的情绪。我期待能快点回家洗个热水澡,冲掉一路的尘土与疲惫;我又厌恶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像被众神惩罚的西西弗斯一样,每日重复着同样的日程。
我突然一个激灵,这不就是家吗?那个熟悉到你厌倦,思念到你憧憬的地方;那个身处其中满腹牢骚,离开之后却又独饮乡愁的地方。
我来自武汉,从呱呱坠地到完成本科学业,二十二载,我一直未曾离开这片土地。武汉九省通衢,但是位于中国心脏的武汉,出国旅游飞哪儿都很远;武汉是百湖之市,坐拥黄金水道,但是被长江汉江割据而成的武汉三镇也各自为营;武汉是全世界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但是整座城市的学术氛围却并不浓烈;武汉曾与上海齐肩被称作“东方芝加哥”,但随着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的还有整个繁华时代的落幕;武汉在近几年的现代化发展中卓有成效,城市打出了“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宣传口号,并宣布每年开放一条地铁线路,然而镌刻在我童年记忆里的小巷也变得不一样了,由地铁施工引发的交通拥堵与环境恶化等问题也苦苦困扰着当地的居民。


武汉
对于武汉的烦闷,我可以像个怨妇一般地讲上一整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搬到德国的埃尔朗根后,我依旧魂牵梦萦着精武的鸭脖,万松园的锅盔烧烤蒸虾和蟹脚热干面,也怀念和摄友们在充满文艺气息的昙华林里端着单反静待夕阳的午后,想念和亲朋好友一边吃一边逛从循礼门走到武汉关,再坐上沿江大道码头上的轮渡一路横跨长江来到武昌的临江大道。这里,我知道看黄鹤楼最棒的角度。
我也说不上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德国小城埃尔朗根当作家的。可能是当我亲切地称呼其为“爱村”的时候吧,可能是当我去邻居丹米斯家取快递的时候吧,可能是上周我和友人莱奥一起包饺子的时候吧,也可能是在公司的一个午休和同事们讨论德国养老金改革时,或者是和室友艾力克斯一边看电视一边吐槽的时候,还可能是当我和朋友们一起共度圣诞节拆礼物的时候……我说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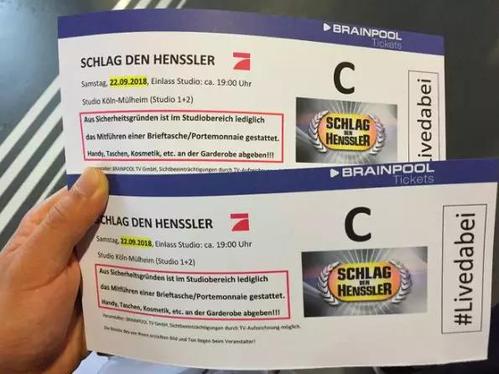
和室友艾力克斯一起去科隆参加电视节目《打败汉森勒》
我的一位台湾好友小马是个作家,曾在菲律宾作预备役两年。他告诉我,离家两年,当他回到他在宜兰的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理发。当时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有一种天涯逢知己但相见恨晚的感动。当我还住在武汉的时候,我对理发也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每次远游后返家,第一件事也常是理发。因为,只有在那条我熟悉的街上,我熟悉的店里,听到我熟悉的发型师,用熟悉的声音说“嗨,你来了”,我才能安心坐上转椅。
德国的理发店大多不适合亚洲人的头型,只能将就去近东的土耳其人经营的理发店打理发型。而其与之服务不相符的价格,直接将我止于门外。所以,我的理发店情结就这样在欧洲终结了。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地,在爱村,我知道市政厅、市图书馆以及电影院有免费的厕所;市中心的白心街上的泰餐厅味道可口但是味精太重;东边医院街上有家叫做“早安”的意大利菜馆,橄榄油质量上乘,披萨又大又薄;市文化中心除了每天都有不同主题的派对以外,出门左走不远就能吃到美味的印度菜,芒果拉西是我每次必点的饮品;除了主街上最大的那家连锁电影院,爱村还有两家艺术院线,一家叫做曼哈顿,另一家叫做白羔羊;比起可以蒸桑拿的西池游泳馆,我更偏爱有标准泳道的霍腾海游泳馆;西门子的蓝楼不用门禁卡就能自由出入,我在那里以超低价买到过不少兜底货;家门口的公交车一个小时两班车,坐29分那班我能更方便地在火车站换乘去纽伦堡的城际列车;就连市政府、主图书馆每天的营业时间我也捻熟于心。
爱村
原来,武汉不是家,有人牵挂的地方才是家。
从武汉的城市森林,到爱村的独栋别墅;从琳琅满目的钢筋水泥,到极目可见的整片天空。武汉很大,我用了二十二年去熟悉这座城市;爱村很小,只需要两年我就能以此为家。在武汉,从汉阳的江滩到武昌的户部巷,走完长江大桥需要半个小时;在爱村,从我位于城市最南端的家,徒步走到市中心的火车站,也需要半个小时。在武汉,我从家走十五分钟去健身房觉得还算挺近;在爱村,超过十五分钟步程的超市,我就会选择开车前往。城市的格局,改变了我对空间距离的感知力;这种对于城市空间感知力的磨砺,同时也让我与整座城市逐渐交融。
从一座位于亚洲的城市搬到欧洲,除了城市规格的不同,还有文化风俗的变化。相比于空间感知力潜移默化的习得,风俗习惯差异的碰撞有时带来的是如触电一般突如其来的惊吓。
记得前段时间和家人通视频,随口的一句道谢让亲人大惊失色,惶恐地说:“你跟我们说什么谢谢啊!这不把我们当外人了吗!”而遥想一年前,我以为我和室友艾力克斯的关系已经铁到足够不用道谢,他却有点儿生气地指责我不懂礼貌。他告诉我,在他小时候父母就教育他,在家事无巨细必须道谢,这样出门了才能时刻铭记于心。吃过母亲做完的一顿可口晚餐需要道谢,父亲开车二十分钟载他去上学也需要道谢,所以当我在餐桌上唤他帮忙将胡椒递过来时,一句被省略了的“谢谢”惹得他不开心了。我连忙解释,在我家正好相反,家人之间几乎不道谢,因为过多的客套反而显得生疏,我们只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保持冗繁的社交礼仪与冰冷的礼貌客气。
同样的文化惊吓不胜枚举。比如我喝汤的声音曾引来同桌朋友的好心提醒,因为吃饭期间只准餐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其他人为的声音都被认为是倒胃口的。我也曾被当作是没有礼貌的,当我静悄悄走进一间教室,因为不想打扰到正在专心思考的同学而没有问好的时候。同行的朋友还指责过我的漠然,当我忘了在她打喷嚏后祝福一句身体安康。而当我在爱村生活过两年后,学会了不着声响地喝汤,我却忘了怎么一边大口扒饭,一边吧唧嘴地夸赞外婆精湛的厨艺;而隔着电话听到母亲打喷嚏,我却因为在中文语境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而干着急。
以前坐飞机从爱村飞武汉,我总说“回家去”;而从武汉飞爱村,我却说“去德国”。现在,我坐在从意大利的特伦蒂诺开往爱村的大巴上。我低头看看手表,心里对自己说,“还有四个小时就到家了!哎!”
作者简介

邹煜,24岁,出生于武汉。本科就读于武汉科技大学,机械与自动化专业,曾担任校学生会新闻与网络部部长。受一场讲座启发,大三突然决定来德国留学,通过一年的时间学习德语备战德福,自主DIY申请学校,于2016年9月第一次踏入德国。目前已在德国的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取得机械硕士学位,硕士期间在校辅导学生编程,并在西门子医疗担任学生工。热爱沙发冲浪、摄影、文学、跨文化交际、街舞、游泳、建模、网页制作、视频剪辑、经营微信个人公众号 “游走在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