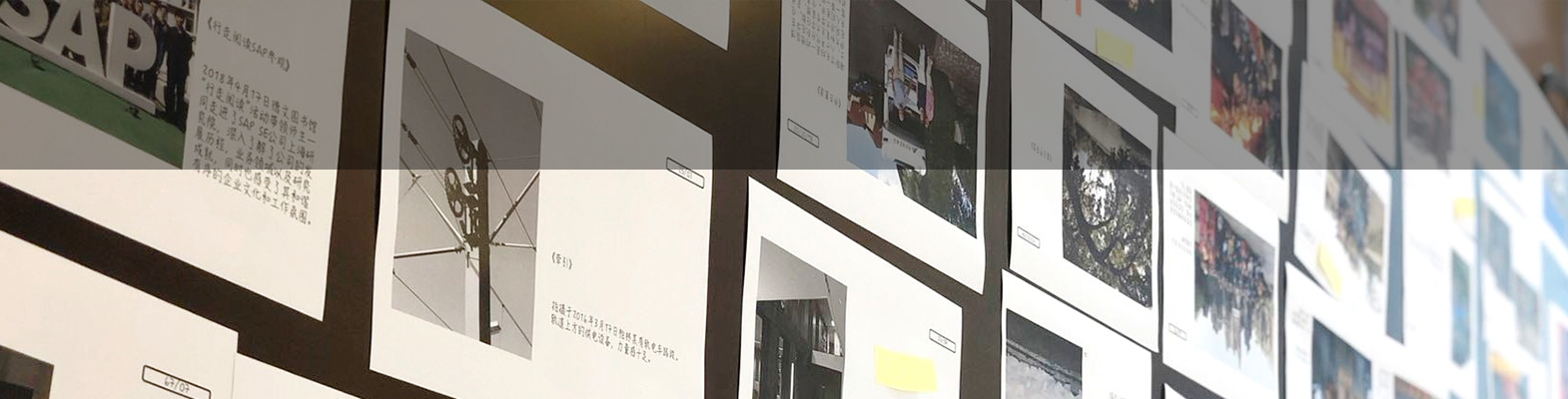熟悉卡夫卡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绝大多数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单身汉”(Junggeselle)的形象出现的,而从根本上说,“单身汉”实际上就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融入社会,自我存在出现问题的边缘人。而该形象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安全感和孤独有着极为强烈的需要”。

《变形记》德文原版第一版 © Wikipedia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变形记》里的格雷戈尔·萨姆萨。从他母亲的口中我们得知:他晚上从不外出,一天到晚只为工作奔忙,他也没有任何娱乐,做木工活就是他业余时间唯一的消遣。而做木工活的一个成果就是他屋内的那个镜框,镜框的画上画着一个“带着裘皮帽围着裘皮围巾的女士”,而这幅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实际上暴露了萨姆萨对于异性贫乏的情欲。事实上,萨姆萨虽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但是他同时也渴望能够与外界接触,能够与其他人建立真正的交往,而他本人对自己的实际状况也并不满意,所以他才会抱怨:“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
因此,在未变形之前,他才特别喜欢在窗户旁边向外眺望,以此来获得那种愉快而又自由的感受,因为这一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他孤独的封闭状态。虽然这里的窗子象征着一种“内与外之间的联系”,并且窗子也为被困于孤独之中的萨姆萨提供了自由眺望的机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窗子同时也是这种孤独状态的保护伞,因为它在孤独者与外界之间设置了一个“界限”,孤独者不可能与外面的世界有真正的接触。窗子实际上可以说是在人物对于孤独的需要与对外界的渴望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平衡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孤独的需要”,而这也是卡夫卡笔下“单身汉”们的生存基调,例如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临街的窗子》里面人物虽然会“随着底下马车的喧闹声被拉入人类整体之中”,但是人物的立足点却依然是窗边,他依然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与人类整体保持着“距离”的局外人。所以,当窗子建立起来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人物的必然选择就是退回到完全的孤独状态。在《变形记》里面,打破这一平衡的正是令格雷戈尔深深反感的他的职业生活。这个“累人的职业”驱赶他“日复一日地奔波于旅途之中”,根本无法享受孤独能够带给他的安静与安全; 而另一方面,他的工作也让他无法与别人建立真正深入的交往,与外界的联系无法顺畅。萨姆萨可以说一直生活在个人与职业的巨大冲突中,他是“为了父母”才“强加克制”自己的内心感受的。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告诉我们,如果现实太令人痛苦,不能忍受,那么被威胁的自我就会因为抵抗失效而投入潜意识冲动的怀抱之内,从而达到脱离现实的目的。潜意识促使萨姆萨幻化为甲虫,完全摆脱了与人类生活的一切直接的关联,退回到完全的孤独状态,从而达到逃避所有冲突与责任的目的。但是在他退回到封闭的孤独状态的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发展自己的可能。开放而又广阔的外部世界离他越来越远,他存在的轨迹越来越局限在他的自身以及他周围狭小的空间,也就是他的小房间,就是与家人的接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正因为如此,“象征与理想化的外界联系”的窗子也就逐渐失去了作用:他再也无法重新领略到从前眺望的那种“自由的感受”,他的视力伴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局限的存在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衰弱,对他而言,窗外所见的只是“一片灰蒙蒙天地不分的荒漠”,而这正是他整个存在状态越来越孤独,越来越逼窄,越来越局促的写照。

卡夫卡木刻像 © http://roll.sohu.com/20120121/n332833561.shtml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萨姆萨就会变得和小说《地洞》里面的那只掘地而居的动物一样,绝对的离群索居,完全生活在自己局限的地洞里以使自己对“安全感与孤独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没有窗子的地洞本身也就象征着与外界联系的断绝。事实上,萨姆萨本人已经认识到,他正在“把那温暖的、摆着祖传家具的舒适房间改变成一个洞穴(……)他可以在那里四面八方不受干扰地爬行,(……)也会迅速而完全地忘记他做人的过去时光”。但是与《地洞》里的穴居动物不同的是,这也正是萨姆萨的不幸,他虽然外形变成了虫子,而且生活习性与存在方式也在慢慢改变,但是他的身上仍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萨姆萨的变形实际上是自我分裂的表征。正是自我分裂的两极之间造成的张力使他根本无法达到通过变形来逃避一切的目的,相反,他的变形正是新的冲突与矛盾的开始,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悲剧的根本原因。
在《变形记》里面,“门”作为与外界联系的另一条纽带却发挥着与“窗”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说“窗”象征着孤独的主体与理想化的开放而又自由的外部世界的联系的话,那么“门”则是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萨姆萨必须首先通过“门”才能去开始他的职业生活,才能来到家庭的氛围当中。如果说房间内孤独的萨姆萨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存在意义上的人的话,那么走向“门”也就意味着他准备去行使自己的社会职能。在变形之后,别人都听不懂他的话(语言是社会间交际的最基本工具),而且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房门打开,这些都表明,他的社会职能面临丧失的危险。等他满怀希望,以为“自己重又被纳入人类圈子”,并且真的把门打开之后,迎接他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全权代理的逃走标志着萨姆萨职业生活的终结;而母亲与妹妹的惊慌失措以及父亲的驱赶则标志着他家庭生活出现的危机,最后父亲那“解脱性的一脚”把他重新送回了自己的房间,同时门也被关上了;而这对于萨姆萨而言也正式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的生涯已经不复存在,他被社会抛弃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萨姆萨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身上仍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穿过那道“门”,重新回到家庭生活的怀抱,但是冷酷的现实却一再地让他失望:父亲的苹果把他打成了重伤,而家人最后都对他感到厌烦,妹妹也不再认为他是哥哥,而是一个“动物”,他们一致同意要把他弄走。就在他刚刚进入自己的房间,门就被从后面关上,还锁了起来,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随着这道门的关闭而彻底断绝。他的妹妹在锁上门的同时,还对父母喊道:“终于进去了!”正是这句绝情绝义的话要了萨姆萨的命,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而他竟然是在“满怀感动和爱意的对家人的回忆”当中死去的,这可真是对冷漠的亲情与残酷的世界的最大的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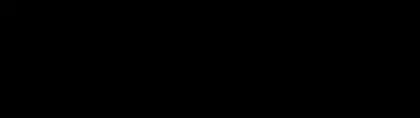
卡夫卡亲笔签名 © 百度百科
作为内与外联系纽带的“窗”和“门”体现的并不仅仅只是内部的主体与外界的联系,它们同时也是外界与内部世界的联系。而在这一点,“窗”和“门”也体现了不同的意义:作为一个一贯以“悖谬”作为基本美学模式的作家,在卡夫卡那里,门内世界与门外人不再是一种接纳与被接纳的关系,而是一种排斥与被排斥的矛盾。《在法的门前》里的那个乡下人永远也无法走进那个原本为他而开的法律的门。《回家》中的叙述者“我”“在门外踟蹰越久,就越是陌生”,而“我”和门内厨房里的人都在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外界与内部之间真正的联系实际上是由“窗”来完成的:《乡村大道上的孩子》里面孩子的伙伴是“跳过窗户栏杆”来找叙述者“我”出去玩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则是《城堡》里索提尼写给阿玛丽亚的信也是让人“从窗口递给她的”,而阿玛丽亚表示拒绝的方式也是“关上了窗户”。在《一个乡村医生》当中,在医生受病人母亲的引诱,将头贴在病人胸口之时,那匹象征“生存的导向”的马正是从通过窗口向他发出警告,以阻止他与死亡接触。
不论是窗内的人,还是窗外的人,“窗”始终都是他们与对面之间最可信赖的依靠,因为“窗”不仅象征着真正的联系,它还带来希望。或许约瑟夫·K最后的遭遇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看到灯光一闪,那儿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人突然从窗户里探出身子,两只手臂伸得老远;他离得那么远,又那么高,看上去又模糊又瘦削。那是谁呢?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愿意解人危难的人?是一个人?是所有的人?还有救吗?(……)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阻挡不了一个求生的人抱有种种幻想。(……)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
专栏作者
梁锡江,1978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矿,血型O,处女座,但从未发现自己身上的处女座特质,也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学了德语,还成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喜欢读书,不求甚解,喜欢听人吹牛,然后默默转化为自己的段子。生平服膺钱钟书与朱光潜两位先生,以他们为目标,如果以后达不到,那就算了。育有一女,狡猾可喜。闲时翻译,总感觉漏洞百出,但心胸又不开阔,爱听鼓励话,重视名利,宠辱皆惊。
金玉“梁”言专栏文章列表
金玉“梁”言 | 译名的困扰—— 从《智者纳坦》与《十日谈》说开去
金玉“梁”言 | 熊孩子
金玉“梁”言 | 我在德国演话剧
金玉“梁”言 | 德语词典里的涉华词条(上)
金玉“梁”言 | 德语词典里的涉华词条(中)
金玉“梁”言 | 德语词典里的涉华词条(下)
金玉“梁”言 | 歌德与母猪
金玉“梁”言 | 德国人的时间意识
金玉“梁”言 | 德国人关于历史的基本划分
金玉“梁”言 | 德国的教师节
金玉“梁”言 | 奴隶主社会?!